43. 为什么公众缺乏条件进行有效思考?再议勒庞主义者的两种大众立场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上次我们讨论了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这个理论虽然并不严谨,但是却符合人们的直觉,尤其是当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由于政治民主化,过去制度安排由少数贵族精英说了算,现在则变成事事都要经过公众的同意。
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粹主义政治精英通过投大众所好而获得权力,带领大众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也是一样,在精英看来,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品味,也由于大众市场的出现而不断拉低。这些就导致了精英对大众的敌视。而勒庞的《乌合之众》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取向。
那么,这样一本精英主义导向的书为什么会在如此强调群众利益和力量的中国流行?我们能否抛开精英的视角、更客观地评判大众的崛起?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这集节目中要讨论的问题。
乌合之众为什么在中国流行?
正是基于我们开头描述的那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大众逐渐威胁到精英的权威,在20世纪初,学术界对“大众”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和研究,形成了一个大众社会理论。所谓“大众”,翻译成英文即mass,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指的是来源广泛的、匿名的、原子化的、数量巨大的中下层群体。在这个基础上,学者们还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关于大众社会的理论。
正是基于我们开头描述的那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大众逐渐威胁到精英的权威,在20世纪初,学术界对“大众”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和研究,形成了一个
大众社会理论
。
所谓“大众”,翻译成英文即mass,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指的是来源广泛的、匿名的、原子化的、数量巨大的中下层群体。
在这个基础上,学者们还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关于大众社会的理论。
第一种大众社会理论来自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大众是来自底层的反叛力量,缺乏理性和长远的眼光,只满足眼前的欲望,破坏了社会秩序,甚至获得社会权力的大众还会造成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的暴政”。
第一种大众社会理论来自
保守主义者
,他们认为大众是来自底层的反叛力量,缺乏理性和长远的眼光,只满足眼前的欲望,破坏了社会秩序,甚至获得社会权力的大众还会造成托克维尔所说的“
多数的暴政
”。
我们可以发现,托克维尔这个观点和勒庞的非常接近,他们都认为大众社会威胁了现有的社会秩序,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驯服和控制这些非理性大众的方法。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在20世纪初兴起,都和这个社会需求有一定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托克维尔这个观点和勒庞的非常接近,他们都认为
大众社会威胁了现有的社会秩序
,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驯服和控制这些非理性大众的方法。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在20世纪初兴起,都和这个社会需求有一定关系。
第二种大众社会理论来自左翼学者,他们认为统治者利用最新的大众传媒,通过精心设计的内容,操纵了大众的心理,使他们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因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每个人都安于现状,只接收来自于精英控制的大众媒体的内容,沉迷于大众文化。
第二种大众社会理论来自
左翼学者
,他们认为统治者利用最新的大众传媒,通过精心设计的内容,操纵了大众的心理,使他们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因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每个人都安于现状,只接收来自于精英控制的大众媒体的内容,沉迷于大众文化。
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反,左翼学者认为大众社会其实强化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也就是精英统治大众的社会秩序。对于左翼学者而言,大众只有摆脱了这种实际上由精英塑造的、商业化的、伪个性化的大众文化,摆脱商业媒体的操控,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反,左翼学者认为
大众社会其实强化了既有的社会秩序
,也就是精英统治大众的社会秩序。对于左翼学者而言,大众只有摆脱了这种实际上由精英塑造的、商业化的、伪个性化的大众文化,摆脱商业媒体的操控,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两种观点的冲突。这种冲突来源于不同的视角,保守主义者从精英的视角出发,从上至下地看群众;而左翼学者从大众的视角出发,从下至上地看群众,所以两者最后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形象,也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中国社会,这两种观点的冲突也非常鲜明。而这种冲突产生,就可以追溯到勒庞《乌合之众》在中国的引进。
在中国社会,这两种观点的冲突也非常鲜明。而这种冲突产生,就可以追溯到
勒庞《乌合之众》在中国的引进
早在1903年,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就在《新民丛报》上刊登长文,专门对勒庞的民族心理学进行引介。1920年勒庞的《群众心理学》中译本问世。当时鲁迅与周作人都在文章中引用勒庞的观点。
尤其是鲁迅,他深受勒庞民族心理思想的影响,他的中国国民性观念,就有一些勒庞的影子。我们在他的很多小说、杂文里,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保守的、平庸的民众、麻木看客、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讽刺,这些都体现出勒庞《乌合之众》对他的影响。
但鲁迅的引述,目的是为了对中国大众麻木无知的这种社会现象加以描述和揭露,从而凸显广开民智的重要性。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引用勒庞,则是用来表明他对于大众和各种政治运动的不信任,认为它们背后都是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他呼吁,要保持理性和个人主义,必须远离这些大众运动。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里的原话是,虽然“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但是“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引用勒庞,则是用来表明他对于大众和各种政治运动的不信任,认为它们背后都是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他呼吁,要保持理性和个人主义,必须远离这些大众运动。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里的原话是,虽然“
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但是“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
”
这之后,在新中国建立后,勒庞在中国被当作资产阶级社会学,因而遭受批评并从大众视野中消失。然而到2000年,冯克利的译本《乌合之众》问世,又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勒庞热”。在今天中国的勒庞热中,也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立场。
一种观点是政治精英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存在乌合之众,所以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要用威权的方式进行统治;
一种观点是
政治精英
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存在乌合之众,所以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要用威权的方式进行统治;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来自自由派的文化精英,他们认为统治者利用了群众的非理性,动员群众反对持不同观点的群体,实行对社会的统治。他们用勒庞来批评国民性、批评民粹主义背后的威权政治。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来自
自由派的文化精英
,他们认为统治者利用了群众的非理性,动员群众反对持不同观点的群体,实行对社会的统治。他们用勒庞来批评国民性、批评民粹主义背后的威权政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勒庞在中国的流行,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语境。此外,我们还会发现,在中国由勒庞《乌合之众》的流行演化出的两种相反立场,跟我们前面说的两种矛盾的大众社会理论非常相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勒庞在中国的流行,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语境。此外,我们还会发现,
在中国由勒庞《乌合之众》的流行演化出的两种相反立场,跟我们前面说的两种矛盾的大众社会理论非常相似。
乌合之众的学说之所以在曾经的西方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此流行,就是因为它对于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可以是有力的工具。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勒庞在西方,由于西方学术界不断地反思、批判和颠覆,他在西方也就渐渐弱了下去。但在中国,却成为了一本经典的书籍,在大众中广泛流行,不断收割一批又一批新的读者。
乌合之众的学说之所以在曾经的西方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此流行,就是因为它对于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可以是有力的工具。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勒庞在西方,由于西方学术界不断地反思、批判和颠覆,他在西方也就渐渐弱了下去。但在中国,却成为了一本经典的书籍,在大众中广泛流行,不断收割一批又一批新的读者。
另外,想再补充说明下的是,关于解读乌合之众的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有一些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对于勒庞的这两种解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本质就是,他们对于群众的看法都过于简单,忽略了群众自己的声音和表达。其实除了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心理同一化的群众外,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社会群体。
另外,想再补充说明下的是,关于解读乌合之众的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有一些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对于勒庞的这两种解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本质就是,他们对于群众的看法都过于简单,忽略了群众自己的声音和表达。其实除了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心理同一化的群众外,
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社会群体
比如,和勒庞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就认为,现代报纸还造就了另一种叫作“公众”的群体。和群众不同的是,公众保持了个体性和理性,他们通过阅读报纸上同样的信息连接在一起,而不是由情绪传染、暗示、行为模仿等相互影响连接在一起。
比如,和勒庞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就认为,现代报纸还造就了另一种叫作“
公众
”的群体。和群众不同的是,公众保持了个体性和理性,他们通过阅读报纸上同样的信息连接在一起,而不是由情绪传染、暗示、行为模仿等相互影响连接在一起。
而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则综合了勒庞和塔尔德的观点,把社会群体划分成三种类型:群众、大众和公众。群众或者聚众就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大众我们刚才也介绍过,就像左翼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数量巨大和原子化的特征,和乌合之众相比,大众是彼此缺乏影响的,他们都受到大众媒介信息的影响。
而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则综合了勒庞和塔尔德的观点,把社会群体划分成三种类型:
群众、大众和公众
。群众或者聚众就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大众我们刚才也介绍过,就像左翼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数量巨大和原子化的特征,和乌合之众相比,大众是彼此缺乏影响的,他们都受到大众媒介信息的影响。
当然,这种看法后来也被证明是片面的,我们后面讲到小群体和人际影响的时候会提到,从上至下地看,好像大众都是分散的,但是从下向上看,会发现大众之间其实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关系。
至于公众,则和塔尔德所说的比较接近,它是围绕着一定的问题——比如报纸上的内容——形成的理性群体。
以上我们提到的群众、大众和公众,都是概念上的假设,那么,我们能否通过逻辑和事实论证大众是否靠谱呢?
李普曼:大众有刻板印象,不值得信任
关于大众是否具有理性,能否信任大众的政治判断,能否接受民主体制的问题,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也就是一百年前,曾经有过一场著名的讨论,主角是两个当时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另一个是著名哲学家杜威。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图源:wikipedia.org
李普曼那个时候刚刚崭露头角,他刚做过揭黑记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宣传军官,还参加了巴黎和会的文件起草。他1922年出版了一本对新闻学和传播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奠基性著作《公众意见》,这个书名也常常被翻译成《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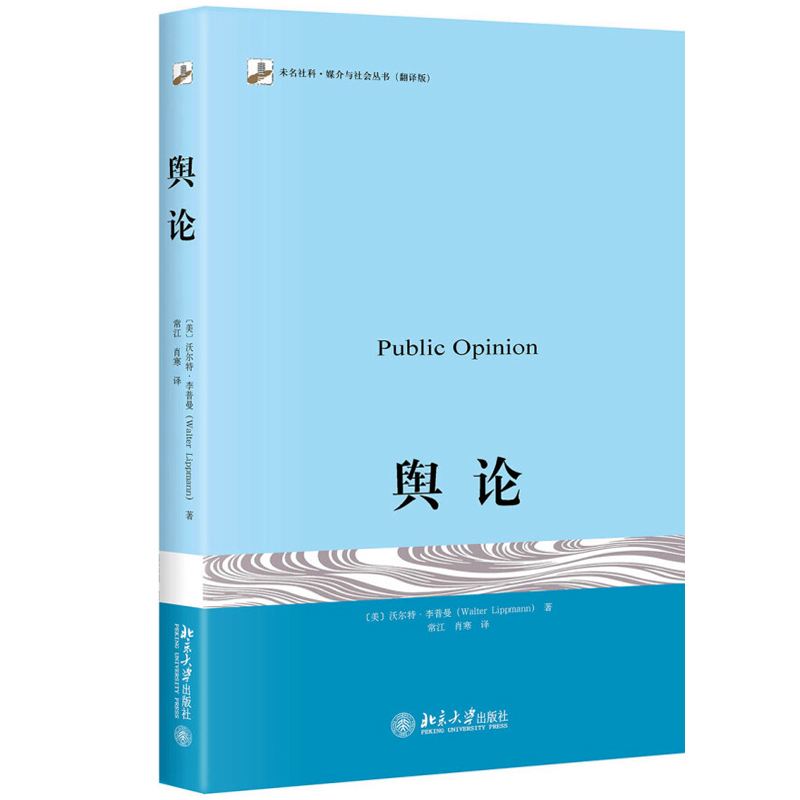
李普曼《舆论(Public Opinion》,图源:taobao.com
这本书虽然是讨论公众的意见,但是那个时代所说的公众与群众其实区别不大,都是指普通民众或社会大众。李普曼认为,大众缺乏必要的能力和时间去关心公共事务,他们容易受到象征符号和图像的操纵,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完全不自知,还在民主政治中草率地做出判断。
在李普曼对于大众的论述中,他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刻板印象”。后来这成为一个我们熟知的认知心理的概念,他认为,人在认知一个新事物前,头脑中不是白板一块,而是根据已往的经验,形成了一个对它的认知框架和期待。在思考和理性介入之前,这个框架和期待就会被强加于新事物之上。新事物与这个期待相符合的部分会被人迅速认知,不符合和矛盾之处则会忽略或者当成例外而降低其重要性。因为这个特点,这种框架会重构我们的记忆。
在李普曼对于大众的论述中,他创造了一个新概念——“
刻板印象
”。后来这成为一个我们熟知的认知心理的概念,他认为,
人在认知一个新事物前,头脑中不是白板一块,而是根据已往的经验,形成了一个对它的认知框架和期待。在思考和理性介入之前,这个框架和期待就会被强加于新事物之上。新事物与这个期待相符合的部分会被人迅速认知,不符合和矛盾之处则会忽略或者当成例外而降低其重要性。
因为这个特点,这种框架会重构我们的记忆。
对此李普曼举过一个例子,在一次心理学会议期间,组织者安排了一场意外,一个人拿枪追逐另一人,从会场人群中穿过。事件结束后让大家去描述刚才看到的这两人的穿戴、开了几枪,以及行为路径时,竟然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歧。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刻板印象来认知和记忆这个事件。
因此李普曼说,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我们所理解的事实,在很多时候只是判断。如果新闻记者和普通受众也像这个会场的心理学家一样,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众意见也会是漏洞百出。
总之,李普曼认为大众缺乏必要的能力,容易受宣传操纵,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把社会决策权交给他们就是个错误,传统的民主制度会把社会引向错误的方向。
那么,怎样使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呢?一是要有准确描述现实的信息,二是要有能够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的人,使用正确的信息来做专业决策。因此他建议政府各个部门从下至上建立起一个收集全面、正确信息的体制,以此替代报纸和其他片面的、碎片化的、不系统的信息渠道。二是政府要找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让他们利用前面那个信息体制获得的有机情报,做出专业的判断。李普曼认为,只有这样,社会发展的方向才会正确。
当然,只有让社会大众都同意并顺从这个方向,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真的按规定的路线行进。这就需要大众媒体发挥恰当的作用,不是像过去那样反映和形成公众意见,而是把专家得出的正确判断灌输给大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意见,然后再通过投票等机制反馈给政治决策。
李普曼的分析,确实丝丝入扣,但是一看结果,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会发现,他虽然从民主进,但是却从威权出,原因是他觉得公众不理性、不专业、缺乏判断能力。最后公众完全变成了看客。
当然,他自己也对这个解决方案不满意,改写了好多遍。后来还又写了一本《幻影的公众》作了补充。但是大家一听书名就知道,他还是不相信公众的能力。他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是,平时程序性的、一般性的决策就可以交给公众决定,反正错了也不会太离谱;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或重大决策时,公众就不要参与了,交给专家和政治精英就好。
总的来说,李普曼和勒庞一样,也认为大众是非理性的,容易受到领袖或者大众媒体的暗示,产生不准确的刻板印象,因此不值得信任。但是细究起来,李普曼和勒庞对大众的看法也存在差异。
总的来说,李普曼和勒庞一样,也认为大众是非理性的,容易受到领袖或者大众媒体的暗示,产生不准确的刻板印象,因此不值得信任。但是细究起来,
李普曼和勒庞对大众的看法也存在差异。
首先李普曼所说的大众的不理性,主要是个体能力不足,而不是在群体中丧失了原本的能力与理性。李普曼所说的大众是原子化的,彼此之间并不会相互影响,而勒庞则认为是个体相互影响造成了非理性。在这一点上,李普曼的群众不是真正的群众,只是一个一个人的简单相加。所以相对于勒庞对群众的看法,李普曼反而退步了。
第二点不同是,勒庞把群众的问题归结为是民族心理、遗传等生物学上的因素造成的。而李普曼则主要是从人的认知的心理学角度,认为大众缺乏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在认知结构上存在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在这一点上,李普曼更接近现代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大众的这种缺陷是后天建构而来的,比勒庞那种大众的非理性本质不可改变的看法更科学,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点不同是,勒庞认为所有人均是群众,不存在能够摆脱群体心理影响的人,我们在上一集提到,这个观点存在着逻辑漏洞,因为照他这么说,居高临下指责大众无脑的人,自己其实也属于无脑的大众。而李普曼则在逻辑上更能自圆其说,他回到了传统的精英与群众的二分,认为专家还是可以摆脱大众的这种无能状态,做出专业、理性的判断。
《公众意见》是李普曼由一个左翼愤青和进步主义者转向自由保守派的第一步,到后来他就越走越远,成为保守派的代表。可以说,在大众是否理性的讨论中,李普曼站在了反对的一端。
杜威:大众值得信任,但需要条件
与此同时,在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则对李普曼在《公众意见》中对公众的看法不满。他认为大众是值得信任的。

杜威(John Dewey),图源:wikipedia.org
杜威在1927年出版了一本《公众及其问题》,在里面他还针锋相对地提出,李普曼所说的公众意见只是原子化的大众的个人意见,而不是公众的意见。因为真正的公众会进行讨论协商,然后形成共识性意见。可见,杜威和勒庞的不同之处在于,杜威把人们看成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单个人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是集体智慧会超越个人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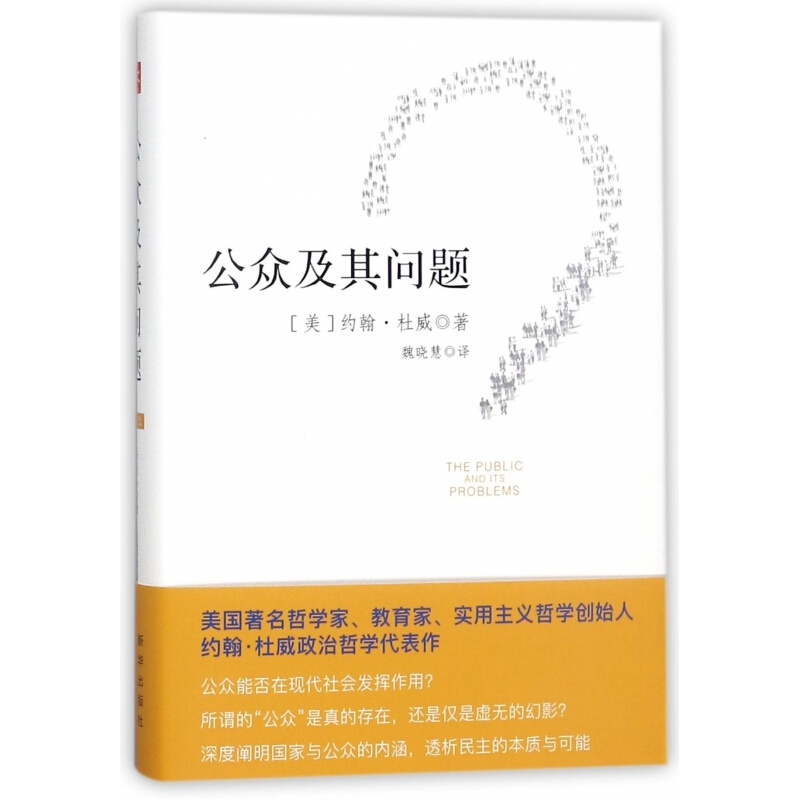
杜威《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图源:jingxi.com
此外,杜威对民主的定义也和李普曼不同,他认为,民主的目的不是要找出正确的结论,而是要实现一种自我管理的生活状态。鞋合不合脚,鞋匠或者专家说了不算,最后还要穿鞋的人也就是公众自己说了算。专家和政治家不能越俎代疱替公众做决定。从杜威这个观点来看,李普曼为了追求正确的决策,最后把民主变成了威权,这就颠倒了手段和目的,忘记了民主的初心。
此外,杜威对民主的定义也和李普曼不同,他认为,
民主的目的不是要找出正确的结论,而是要实现一种自我管理的生活状态。
鞋合不合脚,鞋匠或者专家说了不算,最后还要穿鞋的人也就是公众自己说了算。
专家和政治家不能越俎代疱替公众做决定。
从杜威这个观点来看,李普曼为了追求正确的决策,最后把民主变成了威权,这就颠倒了手段和目的,忘记了民主的初心。
所以杜威认为,大众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并不像李普曼所说的那么悲观,只要专家能够利用媒体向公众准确传达信息,同时允许公众利用大众媒体进行讨论协商,大众媒体就可以促进民主的实现,而不是沦为上传下达的宣传工具。
所以杜威认为,大众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并不像李普曼所说的那么悲观,
只要专家能够利用媒体向公众准确传达信息,同时允许公众利用大众媒体进行讨论协商,大众媒体就可以促进民主的实现,而不是沦为上传下达的宣传工具。
所以,杜威和李普曼在大众是否理性、是否值得信任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意见相左。不过后来有人提出,李普曼和杜威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争论,杜威在行文中并没有明确地以李普曼的观点作为靶子,李普曼后来也没有回应杜威。但是杜威的上述看法,也的确代表着进步主义者对于保守主义者的批评。
另外,杜威的观点也回应了上次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大众其实并没有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的那种非理性的本质,我们每个人都是大众中的一员,之所以会做出错误判断,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而是我们缺乏运用理性的机会与条件。
另外,杜威的观点也回应了上次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大众其实并没有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的那种非理性的本质,
我们每个人都是大众中的一员,之所以会做出错误判断,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而是我们缺乏运用理性的机会与条件。
当然,有人会说,难道个体自己就完全没有责任吗?确实,每个人都需要提高自己的素质,但是以个人素质为由,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个体身上,忽略政府和社会应该提供的条件,同样也是不公平的。
除此之外,还想再次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还需要把大众放在今天的传播技术下看,现在的技术条件,已经使得群众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变得更加进步,群众也在进化。对于传播学来说,看到群众的不同侧面,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现在,勒庞的幽灵还在以不同形式复活,比如说那些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的人那里,勒庞的幽灵又以某种形式复活。这些人认为,目前的大众已经对事实不感兴趣,而是以感情与立场为根据,形成自己的判断。他们没有耐心和能力去探究真相。社交媒体上大量虚假信息、误导信息的传播,以及自上而下的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但是按照我们前面的讨论,其实问题未必完全出在民众那里,而是缺乏对技术的有效使用和政治文化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把责任推给群众,就是回到了勒庞的老路上,现在该做的,应该是思考为什么群众缺乏条件和资源进行有效思考。
好,我们对于群众与传播的关系就先讨论到这里,下几次节目我们会讨论一个很受关注的群体传播现象——传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