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谁说“女司机”不会开车?在传播霸权的压抑中升华为顺民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上次我们讲到传播中具有超功利的游戏特质,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和自由的体验。但是,传播并不总是让我们感觉到开心愉悦,甚至有很多让人觉得不舒服和压抑的时候。
比如女性就会经常对媒体上传播的一些信息感觉到不满,因为新闻中常常会强调女性的性别,而不会强调男性性别,比如“女大学生””女老师““女贪官”“女司机”等,同时和男性相比,新闻会更强调女性的年龄、外貌和身体特征等。

网络搜索“女司机”关键词出现多条新闻
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在一次节目中,就对主持人撒贝宁把自己介绍为“女科学家”表示了不满。认为这种说法让人很不舒服。对性别的强调可能暗示她是以女性身份获得这个职位,而不是靠专业能力。
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在一次节目中,就对主持人撒贝宁把自己介绍为“女科学家”表示了不满。认为这种说法让人很不舒服。
对性别的强调可能暗示她是以女性身份获得这个职位,而不是靠专业能力。
此外,当新闻中涉及女性时,女性会被作为主语或者核心内容,当女性是犯罪主体时,主语就是女性,比如“女司机导致XX事故”,但当女性是被害者时,也会用被动句来强调“女大学生被XX人杀害”,而不是强调施害者。
有时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让人不舒服的表达,可能是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强化,比如倾向于歌颂女性任劳任怨,为家庭付出这类事迹。你说它不尊重女性吧,表面上也不是,毕竟在赞扬,但是却树立了一个刻板印象,好像女性只有在家庭奉献的才值得被关注,她的事业和工作则提及较少,这与男性在媒体中呈现的形象正好相反。这种情况可能常常让人感觉不适,但是又没法反对。
这样的不适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一集要谈到的传播与权力的关系。这一集会有些长,话题也比较严肃,我希望可以系统地谈谈。但归结起来简要地说就是,传播既可能是权力的表征,也可能就是权力本身。
说服性传播
传播与权力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介绍。第一个层次是修辞中的权力。第二个层次是政治经济的权力。第三个层次是文化的权力。
我们先来看修辞中的权力。在《权力论》中,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把权力定义为三种:即武力、操纵与说服。大众传播就成为第三种权力也就是“说服”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说服”,是通过说服性传播,也就是修辞,来进行的思想控制。不过,说服并不是强制,而是通过逻辑、语言的力量与情感的操纵,达到目的。而且,说服也并不总是通过语言,行为的展示也很重要。
比如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就曾提出过一个“软权力”(软实力)的概念,他讲过一个故事,说北风和太阳看到一个行人穿了很多衣服,就打赌,看谁能有本事让他把衣服脱下来。北风拼命吹,想把行人身上的衣服吹掉,结果反而导致行人把衣服越裹越紧。换太阳上场,太阳则暖洋洋地照射着行人,让他热得出汗,于是自己就主动地把衣服脱下来。在这个故事里,太阳就是一种软权力,虽然它不像北风那样强迫人,却让人主动做出有利于双方的选择。

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
这种“软权力”就是除了语言的劝服外的另一种说服的形式,也就是它可以表现为由一种制度、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先进性所产生的吸引力。比如美国的科技、生活方式、通俗文化受到全世界大众的喜爱,这就会令人产生好感,愿意主动追随。这也都是说服性传播的体现。
全球文化殖民
前面说的还只是第一个层次,也就是修辞上所体现出来的权力,那政治经济上是怎么体现出来的?这些权力的来源,主要是来自统治群体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所有权的控制,也会使大众传播的结构和内容中隐藏着看不见的权力控制,可以说,政治经济的角度是最明显的隐形权力。
前面说的还只是第一个层次,也就是修辞上所体现出来的权力,那政治经济上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这些权力的来源,主要是来自统治群体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所有权的控制,也会使大众传播的结构和内容中隐藏着看不见的权力控制,可以说,政治经济的角度是最明显的隐形权力。
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甚至有过非常极端的表述,他说:“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的是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甚至有过非常极端的表述,他说:
“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的是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新闻媒介可能享有一些独立性,但是在整体的意识形态和立场上,媒体反映的还是它的所有者或者所有阶层的利益。而从报纸时代就研究美国媒介所有权垄断的学者巴格迪基安也的确发现,美国媒介的垄断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这些年,媒介越来越集中到几个主要媒介集团手中。
这个现象在国际传播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自由传播为由,依靠强大的信息资源与媒体实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了大量它们的文化产品和新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在国际传播方面因为处于失语状态,只能被动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息。
这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传统文化的式微、和身份认同的危机,甚至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传播权力进行的全球文化殖民。
这种现象可以对应到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概念,这个词汇在修辞上就将资本主义的文化影响与它们的经济殖民联系在了一起。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斗争中,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成为了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诉求。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保护主义的做法,会妨碍了全球的自由信息流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场斗争的结果,不出意外,最后是以美英1984年愤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结束。但由于缺乏美英的参与,新秩序的建设进入僵局,不了了之。一直到今天,这种矛盾依然存在。虽然2003年美国回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2018年,在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又再次退出了该组织。
另外,近年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全球化,甚至有人认为就等于美国化、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所谓的全球化与后发展国家,也包括法国这样的其他发达国家之间仍旧存在文化传播权力方面的冲突。
话语就是权力
除了前面讨论的说服、传播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两种比较容易理解的传播权力外,传播符号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运作。
这个观点可能有点违反常识,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权力意味着强迫,比如在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等学者那里,权力被定义为让别人做出违反自己意志的行为。它往往意味着背后有某种物质性的力量在保证权力的实施,如果拒绝这种权力,可能导致直接的后果。就像如果你不遵守组织的规则,严重的可能会被开除,如果不遵守国家的法律规范,还可能受到国家机器的镇压。
但是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学者们对权力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传统的宏观政治经济的视角,转向了微观话语结构的视角。
比如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就把权力泛化为一种弥散的、隐形的结构性力量。在《规训与惩罚》一书里,福柯把权力定义为一种在描述、定义、甄别、分类、检查、监控、规训、忏悔等行为中行使的技术,它无影无踪,但却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的每一个层面,形成复杂的权力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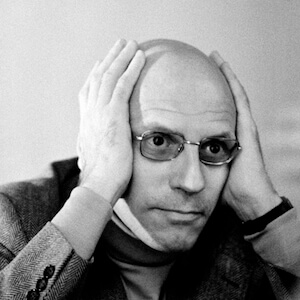
米歇尔·福柯
通过这样的方式,现代的权力不再是由统治阶级从上至下地强加于人,而是在话语结构中,从下至上地重新组织社会。这种权力无从追溯,所以福柯并不关注权力的来源和操控者,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权力的行使方式和技术上。这种技术就是知识。权力会通过不断生产出所谓“客观的”知识,使自己悄无声息地被合法化,导致话语和实践、知识与权力已经很难被截然分开。
通过这样的方式,现代的权力不再是由统治阶级从上至下地强加于人,而是在话语结构中,从下至上地重新组织社会。这种权力无从追溯,所以福柯并不关注权力的来源和操控者,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权力的行使方式和技术上。
这种技术就是知识。权力会通过不断生产出所谓“客观的”知识,使自己悄无声息地被合法化,导致话语和实践、知识与权力已经很难被截然分开。
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福柯式的现象。比如怎样确定什么情况是感染,区分不同程度的感染者、不同程度的危险性,如何对地域的安全性进行分类定级,哪些情况需要隔离,隔离又分成哪些等级,分别对应什么人,如何确定隔离时间和安全时间,如何确定核酸的有效期等等。
这些既是专业知识,也是一套规训技术和实践,这里面既有客观的科学知识,也有政治,权力就通过不断生产出所谓“客观的”知识,使自己悄无声息地被合法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防疫知识话语权力网络。

图源:深圳新闻网
所以福柯提出了一个知识就是权力的概念,认为知识与权力已经无法清晰的区分,二者甚至就是一回事。通过“规训”、“分类”、“甄别”、“检查”、“忏悔”这些知识和技术,权力不仅成功地驯服了身体,而且深入到人的内部,制造了主体。所以人们以为的那个自我,往往是被权力所驯服的自我。
从福柯的角度来看,特定话语结构的形成与扩散、凝视、忏悔等等这些传播现象,都与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而且福柯的权力概念还打开了新的空间,他超越之前人们关注的消极的、压迫、禁止的一面,发现了权力还有主动的积极的、生产性的一面。它不再是强制性的,不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行动,它也可以是无法分辨的言说。
这也是这种权力的隐匿性所在,我们常识中行动与言说的二分法往往是导致我们理解传播权力的一个障碍。一般人会觉得,坐而论道只是耍嘴皮子,符号并不如行为那样对现实有影响。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语言符号和表征同样具有行为的效力。其实也就是我们开头讲的那个有所指的女性形象的案例里,我们常常觉得不舒适但也不知道不舒适在哪里的原因。
这也是这种权力的隐匿性所在,我们常识中行动与言说的二分法往往是导致我们理解传播权力的一个障碍。
一般人会觉得,坐而论道只是耍嘴皮子,符号并不如行为那样对现实有影响。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语言符号和表征同样具有行为的效力。其实也就是我们开头讲的那个有所指的女性形象的案例里,我们常常觉得不舒适但也不知道不舒适在哪里的原因。
关于这一点,英国的语言学家奥斯汀有过精彩的论述,(John Langshaw Austin,1911—1960),他说,我们除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沟通外,还可以用语言来做事。比如婚礼上“我愿意”这句话就意味着礼成,这个承诺就完成了“结婚”这一行为,他把这种用言语来完成的行为称为“言语行为”(speech act),类似的行为还包括通知、命令、警告、阻止、答应、承诺、担保、道歉、祝贺等。
还有我们前面在谈到传播的传递观时,讲过一个元话语的概念。说的其实也是在任何字面意思的背后,都存在着说话者的意图,比如要表示友好、攻击、讽刺等,说到底,这些也都是行为。所以言语与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分得并不是那么清晰。在看似工具性的语言背后,其实蕴含着支配关系,比如会议的主持人可以宣布“现在散会”,而会场上的服务人员却没有宣布的权力。
这样的差异,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说法,就是一种“符号暴力”。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同样也是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活动中实现的。”因此语言及符号不仅仅是权力的工具或者中介,它本身可能就是权力。
这样的差异,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说法,就是一种“符号暴力”。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同样也是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活动中实现的。”
因此语言及符号不仅仅是权力的工具或者中介,它本身可能就是权力。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所有符号均建立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如好坏、高矮、长短、黑白等。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则是在索绪尔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立的双方在现实的文化中并不完全平等,而是具有某种价值判断,比如形容人的这些黑/白、高/矮、美/丑、胖/瘦的对立符号。它们之间的差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我们会赋予某一概念一个高于另一概念的价值。比如我们觉得白比黑好,瘦比胖好,在这种二元对立之中就发现价值观悄悄渗透于其中。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所有符号均建立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如好坏、高矮、长短、黑白等。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则是在索绪尔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立的双方在现实的文化中并不完全平等,而是具有某种价值判断,比如形容人的这些黑/白、高/矮、美/丑、胖/瘦的对立符号。
它们之间的差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我们会赋予某一概念一个高于另一概念的价值。比如我们觉得白比黑好,瘦比胖好,在这种二元对立之中就发现价值观悄悄渗透于其中。
德里达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说这些对立的符号并不会同时出现,其中一方常常缺席。而缺席的符号也构成了一个隐形的判断。比如我们表扬某个行为,其实也就意味着否定了与其对立的行为,这一对立的行为在表达中也许并不出现。这种自然而然的叙述常常掩盖了现实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对女性家庭表现的赞扬,其实就隐含了对女性工作表现的缺失。
意识形态霸权
以上说的,就是为什么在传播中会存在权力。当这些传播中的权力符号被组合运用时,最后就会产生意识形态上的霸权现象。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利用强制性的权力来管理社会,而是转向通过传播活动建构起符合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其统治。“意识形态”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不过一般人常常把它看作是负面的、错误的、虚假的思想。好像只要揭穿它,就可以得到解放。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利用强制性的权力来管理社会,而是转向通过传播活动建构起符合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其统治。
“意识形态”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不过一般人常常把它看作是负面的、错误的、虚假的思想。好像只要揭穿它,就可以得到解放。
然而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他认为它是“个人对于他所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是一种人们无法摆脱的认识世界的框架。意识形态这一国家机器通过召唤,作用于人的潜意识,塑造了人的主体,同时令其成为意识形态的臣服者。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控制,由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很难摆脱。
另外还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和阿多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发现以大众传播为载体的文化工业其实是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
大众传播把标准化的、伪个性化的和陈腐的观念推广到劳动大众那里,使他们在压抑的升华中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流水线上的顺民,不仅在八小时以内,而且在八小时以外的文化消费领域也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所谓的大众文化根本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文化,完全是资产阶级控制大众的文化工业。
总而言之,学者们认为这些都是统治阶级将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符号,编码进传播内容之中的尝试,希望受众在接受这些内容时,领会和解码这些意识形态。这样,统治者不必天天喊口号,就能潜移默化地将不利于受众的观念,变成他们的常识。就像我们在本讲开头提到的大众媒体上的那些涉及女性的表达中,就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将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隐藏其中。
权力中暗含着对权力的反抗?
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绝望?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在他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中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思路。
他说,虽然意识形态的统治是一种符号特权,那么反过来,这种符号传播出去后,在受者那里也享有一个优先解读的特权,受者完全也可以用不同于编码的方式解码,也就是说,这个受众解读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和传播者不一样的“结构性的多义”。大众传播的编码与解码,其实就是语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在话语里面蕴含着权力的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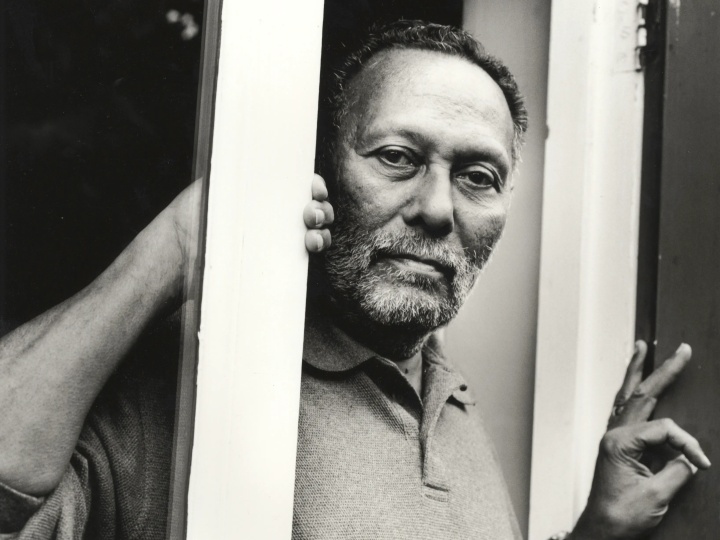
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疑问,虽然这样一种看法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人难道就不能反抗吗?好像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统治,完全没有能力拒绝,难道就不能不听不看不接受吗?进一步,我们还会问,如果公众能够意识到大众传播之中的这些意识形态,是不是就不会被控制了呢?比如说,要是女性能够看出前面提到的那些表达中,存在歧视,是不是就可以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呢?
倒还真有学者回答这个问题,按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说法,他会认为结果并不乐观。他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意识形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你明知道传播内容中存在意识形态,但是也找不到理由反抗,就像有些人说的,“这些话如此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
葛兰西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方面依赖强制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在合理性上依赖于意识形态的霸权(hegemony又译为“文化领导权”)。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暴力不同,霸权重视的是文化方面的控制。霸权的推广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它是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妥协与合作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换句话说,是我们自己同意被控制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对女性家庭工作的赞扬,这就是一种文化式霸权:“都表扬你了,你还能不满吗,你还想怎样?难道要批评你吗?”
换句话说,是我们自己同意被控制的。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对女性家庭工作的赞扬,这就是一种文化式霸权:“都表扬你了,你还能不满吗,你还想怎样?难道要批评你吗?”
糟糕的是,还有更隐蔽的霸权。有的女性主义者就敏锐地发现,在生孩子的全过程中,好像只有一套医学术语来来描述自己的经验,包括各种培训和知识,都是用纯粹客观视角来表达,而这些医学术语主要是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描述生产过程,这也是一种从男性视角出发的知识,缺乏女性从自己主观感受视角进行的描述。这也是一种失声,导致女性在表达、回忆生产过程时,被剥夺了自己的主观体验。
糟糕的是,还有更隐蔽的霸权。
有的女性主义者就敏锐地发现,在生孩子的全过程中,好像只有一套医学术语来来描述自己的经验,包括各种培训和知识,都是用纯粹客观视角来表达,而这些医学术语主要是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描述生产过程,这也是一种从男性视角出发的知识,缺乏女性从自己主观感受视角进行的描述。这也是一种失声,导致女性在表达、回忆生产过程时,被剥夺了自己的主观体验。
有人可能会说,那既然我知道了,我以后就用我的方式来跟医生沟通,但问题是在于,即使女性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平等,似乎也很难反抗,因为这属于医学专业,你在医院,已经就默认了你当然要接受科学的表达方式,否则就容易发生意外,出了意外,痛苦的是谁?这似乎又是一个常识性的霸权。
于是女性的生育,相当于是在主观经验与表达上被双重压抑。反过来,这种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的二分乃至符号化地对立,也进一步强化了男性知识的主导权。
而且,如果我们把前面讲的这个案例里的女性换成其他人群,比如贫困群体、农村居民、身体残障群体、少数族裔、LGBT群体等,再把生产过程换成这些群体的经历,是不是也同样成立?可以说这种霸权随处可见。
好,这一集就讲到这里,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能够意识到在我们的媒介生活中,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其中还蕴含着许多显性或隐性的权力,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及了其中一些,还没有包括嵌入到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中的权力,还有体现在身体语言中的权力等等。
这些内容我们后面会展开讲,如果你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其他我们没有提及的传播中的权力,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会讨论作为互动与共享的传播。下次见。
推荐阅读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
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裘志康译,华夏出版社,1989.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
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34~1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345~3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