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当我们在收看李佳琦直播时,我们在看什么?传播与身份认同的塑造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大家小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年的春节,一个全家固定的仪式,就是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虽然这几年我们对于春晚的关注,已经大不如从前,但大家是否思考过,为什么要举办这些国家、社会层面大的仪式或是典礼,它们在传播上的意义是什么?

春晚经典小品
或者说看北京的奥运会开幕式,体育比赛中中国选手获得奖牌的时候,为什么会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愉悦,好像突然和电视里毫不相关的人甚至是更大层面上的国家,突然就连接在了一起?

北京冬奥会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种新的传播观念,也就是传播作为一种共享,它可以来解释,这种仪式性的传播是如何塑造身份认同的。
在我与你的共享中相遇
我们先来说下这种观点的由来。它涉及到我们如何跟其他人相连接,如何建立跟他人的关系。
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曾提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它”的关系,另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

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
在“我与它”的关系中,周围的人和事物都被当成是与“我”相分离的对象,是与我相对立的客体,这样的对立,导致我们常常用理性和因果的关系把它们放到时空网络中把握,并且倾向于以“我”为中心,利用它们,来满足“我”的需求。
前面我们讨论的那些作为工具的传播,看待关系的视角就是这样的方式,它以传播活动的效率来作为衡量传播活动的标准。这种传播的诉求,也常常是以传播者为中心,把他人作为征服对象的传播。
而在“我与你”的关系中,“我”与“你”不是分离的,而是结为一体的,“我”便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来建立“关系”,也不会只是用理性来分析“你”,而是以“我”整个的存在、全部的生命来与“你”相遇。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你”就超越了时空网络,不再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而具有永恒性。“我与你”的关系在这种永恒中,也就摆脱了相互利用的框架,实现了人的存在价值。
虽然这一理论听上去有点理想化,甚至带有深厚的宗教哲学色彩,但是却给世俗世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真诚地面对他人、面对自然?
布伯认为,我们不应过于功利,而应从“我”与“你”相遇的偶然性中,生活在“你”的世界中,在共享中理解对方。这就为后来的人提出“共享和互动”式的传播奠定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和宗教意味的基础。共享式的传播看待关系的方式,就是我与你的视角。它的目的,是要通过传播建立共同身份,而不再把他人看作是一种区别于自己的力量。
民主制度无法实现?
“传播是共享”这个观念,首先是由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的。当然他不是从布伯那样的精神世界里的思辨来看待传播,而是基于现实,尤其是从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角度来看待传播与共同体的关系。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
杜威的观点是在批判新闻学家李普曼的观点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先来简单看一下李普曼说了什么。
李普曼有本书,叫《公众意见》,在这本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名著中,他说,现代的民主制度中,公众的看法起了决定作用。因此要实现民主,前提条件是保证公众的意见正确无误。那么,要想做到让公民的看法正确,一是要让公民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二是公民要有能力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专业的判断。
但是李普曼认为这两个条件在现实中都很难实现。他也总结出了难以实现的原因,比如说媒体的认知缺陷和外界的限制,会导致新闻媒体其实无法准确地反映世界,同时,政府和组织的宣传、审查,也会使得信息真假难辨。
另外,公民其实也并不理性,他/她们不仅喜欢按照刻板印象理解世界,同时也缺乏时间和专业知识。如此种种,都会造成公民对社会现实的无知。因此,就算媒体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制,民主制度仍然无法真正实现。
民主就是共享与传播
那杜威是怎么看李普曼这本书的呢?在李普曼的这部《公众意见》出版后,杜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是用文字写成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控诉。但另一方面,他一直对李普曼的结论不甚满意。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就没有实现民主的办法了?于是在6年后的系列讲座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杜威觉得,除了要求新闻媒体和专家尽可能地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首先意识到,外部世界并不是一个可供我们准确复制的图像,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或者“事实”摆在那里。因此,要想获得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除了用“眼睛”看以外,更重要的是用“耳朵”听。
用耳朵听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民主或社会并不是完全像李普曼说的那样,存在于一个客观真理中,我们只能依靠每个个体自身的能力和理性去认知这个真理。
相反,民主存在于传播与交流中,我们可以依靠的其实是大家的协商与同意。在这里,杜威强调的是交流与聆听。他认为,传播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而不是共享内在的意识的秘密。李普曼那种要求每个公民全知全能,这根本就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大家正在共享着一些东西,正在认同着一些东西。
说到底,杜威的看法是,民主不意味着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寻找共识。这就像鞋子合不合脚,不是鞋匠(专家)说了算,而是穿鞋的人说了算。民主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共同体自我管理的生活方式。因此,传播在杜威的民主理论中,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民主就是共享和传播。
说到底,杜威的看法是,民主不意味着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寻找共识。
这就像鞋子合不合脚,不是鞋匠(专家)说了算,而是穿鞋的人说了算。民主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共同体自我管理的生活方式。因此,传播在杜威的民主理论中,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民主就是共享和传播。
理性交往的结果,就是真理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üergen Habermas,1929—)深受杜威这些观点的影响,并且把交流的理性看成实现社会制度层面的民主的基础。

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倡者哈贝马斯
在他看来,传播的目的不是使传受双方在意义上和意图上达成一致。人们可以通过传播获得共识,只要保证参与者具有理性,能真实、正确和真诚地彼此进行交流,就可以最终达成传通的理想境界。
哈贝马斯对交流的有效性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表达真实:交流者所说的是真的;二是(道德)正确:谈话内容符合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三是真诚或诚实:交流者的言辞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通过传播,我们可以实现相互理解,达成共识。这种交流本身就能够最终实现理性对话。所以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同样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真理,通过理性交往后被人们认可的,就是最后的真理。
这里还可以用一个经典的故事来加以说明。有甲乙两个强盗要分一堆财宝,应该如何分配呢?如果按照客观的市场价值平均分,是不是最没有争议的方式?但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按客观的市场价值均分,尽管这看上去公平,但总会因为个人喜好造成争议。最现实的方式是,一个人分,另一个人选。分的人认为自己做到了完全公平,选的人觉得自己选择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尽管这种方法未必如第一种方法精确客观,但肯定争议最小。因为双方都获得了自己认为最公平的结果。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和杜威一样,也在公民交流与协商中找到了实现民主的可能路径,是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提倡者。
对话传播成立吗?
当然了,上述关于对话与民主关系的观点也不乏有人质疑。比如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就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日常对话与政治协商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基于关系,后者则是基于解决问题。
基于关系的对话,重点是维系关系,并不太会较真,也没有什么规则,通常我们是自愿的,愉悦的。就像我们在家庭内部的交流,不是讲对错,而是讲态度。但是基于解决问题的政治对话,则是功利性的、有规则的,会不断争辩,互不相让,通常并不让我们开心。而且,民主的基础其实就是这种并不浪漫的争辩,而不是那种理想化的对话。
这样看来,把对话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确实有可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可能实际情况并不是因为对话的理性平等促进了民主,而是因为民主文化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才让普通对话变得更有理性。
另外法国哲学家南希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杜威和哈贝马斯的对话民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共识无法达成,也没有必要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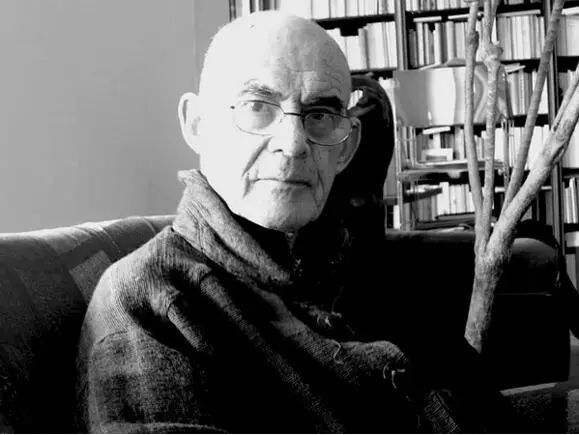
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
他的理由是,分享本身包含着两个部分,分离与参与。分离是主体的分离,参与是交流的参与。任何交流或交往都是基于分离之上,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不确定性、他异性,也不会有交流与传播的冲动,这是传播的基础。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传播与交流不可能完全消除差异,如果没有差异,也就不会有传播,也就是说传播与共识,互为矛盾。
因此,共通体或者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完全同一,有着相同的观点和目标,相反,分离是内在于交往和共通体的每个成员的。共通体中存在着一种“分开的接近”,正因为存在分离,才产生了接近的需求。南希认为,虽然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很难实现,但是身体的在场与联系或可成为构成“共通体”的基础。
因此,共通体或者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完全同一,有着相同的观点和目标,相反,分离是内在于交往和共通体的每个成员的。共通体中存在着一种“分开的接近”,正因为存在分离,才产生了接近的需求。南希认为,虽然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很难实现,但是身体的在场与联系或可成为构成“共通体”的基础
。
在共享传播中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前面讲的这些关于传播与共享的讨论,或是争议,主要是从共享、对话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看传播带来的共享。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1934—2006)受到传播学之外的文化人类学、现象学、及诠释学等人文传统的启发,也发展出了跟前面讲的不一样的共享的传播观念。
我们来看他对传播的定义,他说,传播就是一个制造、保持、修补和转换现实的象征性过程。通过传播,一定群体的人们共享民族、阶级、性别身份、信仰等,换句话说,他们共享着相同的文化。由此,传播不仅塑造和定义着“我们”,还把“我们”与“他们”区别开。
这种传播塑造“我们”的功能,凯瑞还打了个比喻,说传播就是仪式。这里的“仪式”并不是人类学中所说的身体在场的神圣的集体活动,而是将传播比喻成共同参与一个世界。这和仅仅把传播看成是一种信息传递的传递观不同。这种传播仪式,是一种对主体的召唤,邀请人们参与到传播中,获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对现实的再现与建构。
这种传播塑造“我们”的功能,凯瑞还打了个比喻,说传播就是仪式。这里的“仪式”并不是人类学中所说的身体在场的神圣的集体活动,而是将传播比喻成共同参与一个世界。
这和仅仅把传播看成是一种信息传递的传递观不同。这种传播仪式,是一种对主体的召唤,邀请人们参与到传播中,获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对现实的再现与建构。
传播的仪式观并不把我们日常所接收的媒介内容或新闻看做是简单的信息,而是把它看做戏剧(drama)。在这场戏剧里,传播不是描述世界,而是描述权力和行动的舞台,我们被邀请参与其中。因此,重要的不是我们通过传播获得了什么信息,而是通过传播,让我们与其他人获得了内在的联系,获得了对现实共同的理解。
如果大家还记得2020年初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大家都被隔离在家的时候,每天我们从手机上读到来自不同渠道的疫情的文字、照片和视频,不断地在微信群里分享着各种信息。在那段孤独的居家时间,正是新媒体上的传播活动,让我们建构起了共同的对现实的理解,也把彼此之间联系在一起,抱团取暖。
如果大家还记得2020年初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大家都被隔离在家的时候,每天我们从手机上读到来自不同渠道的疫情的文字、照片和视频,不断地在微信群里分享着各种信息。
在那段孤独的居家时间,正是新媒体上的传播活动,让我们建构起了共同的对现实的理解,也把彼此之间联系在一起,抱团取暖。
同样地,传播还可以塑造民族共同体。按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来说,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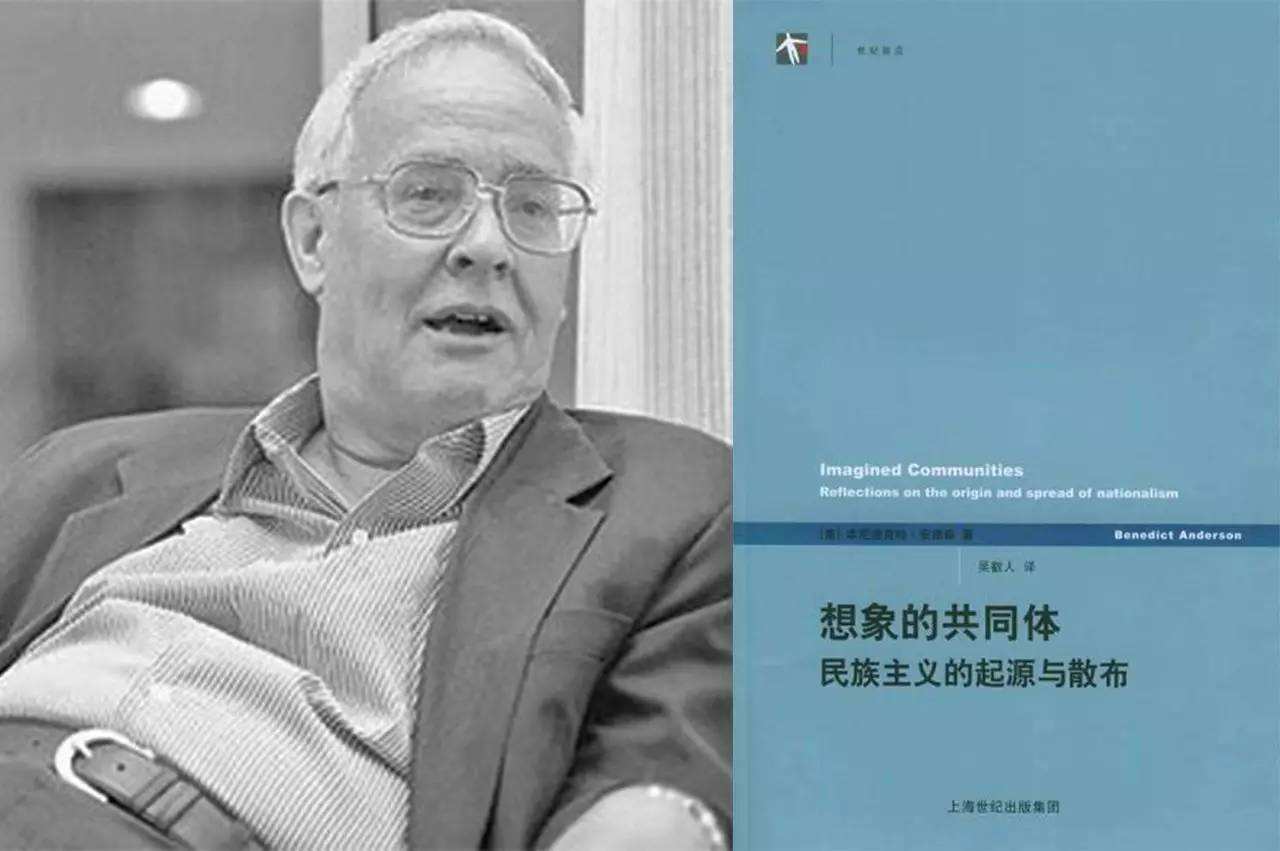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和传统的共同体的不同在于,传统的共同体是基于面对面亲身接触形成的,常常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内。比如一个几十个人的班级或者公司,人人都相互认得,这就是个典型的传统共同体。
但是安德森发现,19世纪的欧美读者,通过阅读印刷媒体(比如用方言写作的大众报纸、通俗小说等),会在读者与作者、其他读者等陌生人之间建立一种想象性的关系。这就是“想象的共同体”,它超越了我们日常的生活空间,把我们和陌生人拉在一起。
奥运会或春节联欢晚会,就是这样的功效。在看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有许多和我有共同身份的人也在同时观看节目和分享这一时刻的经验,这也会形成想象性关系。这种共同想象就成为了区分“我们”和“他们”,成了建构个人身份的集体依据。
在交流中生成意义、记忆与文化
传播交流可以形成共同文化,我们的群体认同,甚至群体记忆,都来自于彼此通过交流而共享的意义。我们的群体记忆有许多种,包括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虽然它们的侧重点不相同,但归根结底,都认为传播交流可以形成共同文化。
集体记忆的提出者哈布瓦赫认为,只有在社会的交流传播过程中,记忆才能被赋予意义和保留下来,否则就会随风而逝。因此不存在私人记忆这个概念,就像最典型的梦境,如果不向人复述或书写下来,只留在内心,很快就会被遗忘。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记忆,都建立在与他人的交流之上,甚至储存在媒介生活的痕迹中,记忆都是集体的而不是私人的。
集体记忆的提出者哈布瓦赫认为,只有在社会的交流传播过程中,记忆才能被赋予意义和保留下来,否则就会随风而逝。
因此不存在私人记忆这个概念,就像最典型的梦境,如果不向人复述或书写下来,只留在内心,很快就会被遗忘。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记忆,都建立在与他人的交流之上,甚至储存在媒介生活的痕迹中,记忆都是集体的而不是私人的。
除了集体记忆外,还有人类学家康纳顿提出的社会记忆。这种记忆与个人记忆(比如潜意识中的记忆)和认知记忆(比如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基模和刻板印象)不同,社会记忆是一种基于实践和身体操演的记忆(比如对骑自行车的记忆,或者如何在高级餐厅用餐的记忆都是这种类型),它是非表意性的身体姿态,是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操演习得的,所以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传播与共享获得。
除了集体记忆外,还有人类学家康纳顿提出的社会记忆。
这种记忆与个人记忆(比如潜意识中的记忆)和认知记忆(比如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基模和刻板印象)不同,社会记忆是一种基于实践和身体操演的记忆(比如对骑自行车的记忆,或者如何在高级餐厅用餐的记忆都是这种类型),它是非表意性的身体姿态,是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操演习得的,所以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传播与共享获得。
后来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又提出了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强调口头交流和集体表征、大众媒体的作用相比,文化记忆更强调物质(比如纪念碑)、强调相关的空间(比如博物馆)、也强调时间(比如各种类型的群体纪念日)等外在物质或符号的表征与联系的功能。
后来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又提出了文化记忆。
和集体记忆强调口头交流和集体表征、大众媒体的作用相比,文化记忆更强调物质(比如纪念碑)、强调相关的空间(比如博物馆)、也强调时间(比如各种类型的群体纪念日)等外在物质或符号的表征与联系的功能。

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
虽然这三个概念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了交流在社会共享意义和记忆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传播可以形成社群、共同身份、文化,这种观念在中国儒家的文化中也受到重视。
比如孔子谈到诗(《诗经》),也就是春秋时的流行音乐时,曾说它可以兴、观、群、怨(《论语·阳货第十七》)。其中的“群”就是结成社会。另外,古时候一直强调的礼乐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传播仪式,当时人们正是通过它们来维护身份秩序。到了今天,传播形成群体的功能仍然存在,不过仪式的内容换了换,变成了春晚、奥运会以及更多平台的电商直播。作为仪式的传播无处不在。

2亿网友观看李佳琦直播(图片来自网友截图)
好,今天我们介绍了许多学者的观点,其实总结为一点,就是认为传播不仅是信息和意义的传递,同时还是群体成员之间建立联系,共同参与现实世界,建立共享身份的活动。
其实,在英语中,传播communication就和共同体、社群community、共产主义communism、共同common具有相同的词根,可以说,传播这个词中就包含着“共享、共同拥有”的意思。所以,媒介生活的重点,也许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我们在一起共同听到了什么、分享了什么,建构了什么。
这一集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进一步介绍作为连接与关系的传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推荐阅读
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三联书店,2002.
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夏可君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詹姆士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比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