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点赞自拍玩游戏的我们,正在为互联网公司无偿劳动?传播行为的商品化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工作与玩游戏、发朋友圈是两件相反的事情。工作是被迫地付出体力与劳力,让人痛苦,而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发个朋友圈、点个赞,都是自愿的和快乐的。但是在当下,有的时候似乎这两者越来越难以分开了。比如说当我们追网综追得比平时工作都辛苦时,那这个过程到底是痛苦还是快乐?在这集里,我就想来讲讲这个话题。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工作与玩游戏、发朋友圈是两件相反的事情。工作是被迫地付出体力与劳力,让人痛苦,而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发个朋友圈、点个赞,都是自愿的和快乐的。
但是在当下,有的时候似乎这两者越来越难以分开了。
比如说当我们追网综追得比平时工作都辛苦时,那这个过程到底是痛苦还是快乐?在这集里,我就想来讲讲这个话题。
我们前面介绍过传播的游戏理论,传播游戏是一个让我们投入的、获得快乐、提升自我的行为。大家可能听说过“游戏代练”或者“金币农夫”,这就是一些电子游戏的玩家有组织地在电子游戏中完成任务,攒下积分,然后换成装备,卖给其他想走捷径的玩家。后来游戏平台也开始将一些装备或皮肤明码标价,卖给所谓的“人民币玩家”。于是这成了游戏平台赚钱的重要渠道。
此外,网上还存在着付费的游戏陪玩业务,一些孤独的玩家,多数是男性玩家,觉得一个人玩没意思,于是在网上付费雇佣陌生的玩家,一般是年轻的女性,一起在线玩游戏。
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都涉及到了商品买卖。那么买卖的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如果存在交换,这里就存在着劳动。而且这些行为里,确实涉及到一种特殊的数字劳动。
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都涉及到了商品买卖。那么买卖的是什么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如果存在交换,这里就存在着劳动。而且这些行为里,确实涉及到一种特殊的数字劳动。
如果玩游戏也可能生产商品,那么即使不涉及商品买卖的网络游戏行为,是不是也是一种劳动呢?它和我们工作时间的劳动是一回事吗,它又生产了什么商品?
还有,像微博、微信、B站,短视频平台、豆瓣等平台,我们被它们吸引,是因为上面有我们感兴趣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都是用户生产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UGC(User-generated Content),但是绝大部分的内容生产者是得不到什么报酬的,那平台生产的商品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作为这些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用户,我们是被剥削了吗?
今天我们就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谈传播劳动和数字劳动的问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经济活动的伦理
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它是如何看待传播问题的。对于政治经济学,大家从小上政治课就接触,应该不陌生。比如大家都背过,商品的价值来自于工人劳动的凝结,而工人在应得的工资外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导致了劳动中的不平等关系,工人被剥削,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和以供求关系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加上了政治二字,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更重视伦理问题,比较关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道德问题与正义问题。同时,政治经济学比经济学产生的时间更早,它不是孤立地看待经济活动。之后的经济学实际上是把经济行为从社会活动中专门拎起来研究。那么政治经济学相反,它是把经济嵌入到社会的历史与具体语境中,从整体上来看待经济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和以供求关系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加上了政治二字,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更重视伦理问题,比较关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道德问题与正义问题。
同时,政治经济学比经济学产生的时间更早,它不是孤立地看待经济活动。之后的经济学实际上是把经济行为从社会活动中专门拎起来研究。那么政治经济学相反,它是把经济嵌入到社会的历史与具体语境中,从整体上来看待经济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中有很多的支脉,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亚当·斯密,其实他同时是一个研究道德哲学的学者,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与其说更像现在的经济学,不如说那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比较大,比较重视商品化与劳动的问题,但是也正是如此,就遗留下了一些问题。
比如,经典的传播研究比较注重内容及其影响,不论是关注心理效果和社会效果,还是关注内容中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是把大众媒介视为一个文化工具,但是却忽视了媒介具有的经济功能,以及媒介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发挥了什么功能。
这个问题既是传统的传播研究的盲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点。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经济活动和媒体的内容生产之间分得还比较清楚,不像今天这两者已经难分彼此,我们前面提到的伪事件、文化工业、社交媒体等都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
这个问题既是传统的传播研究的盲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点。
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经济活动和媒体的内容生产之间分得还比较清楚,不像今天这两者已经难分彼此,我们前面提到的伪事件、文化工业、社交媒体等都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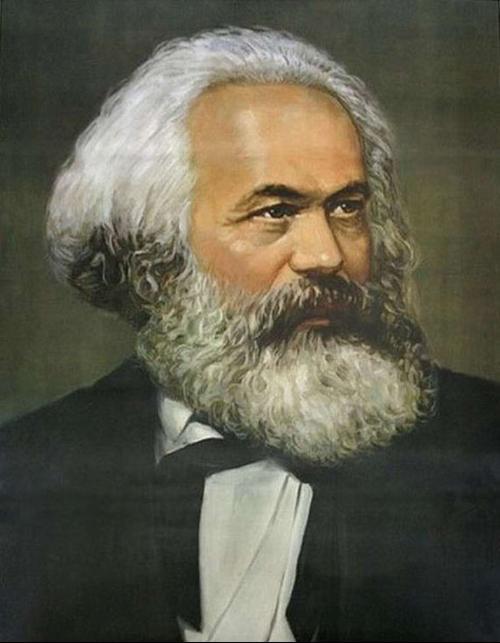
卡尔·马克思,犹太裔德国哲学家、革命理论家,图源:ifeng.com
马克思关注的商品和劳动,主要还是生产性劳动及其商品化的过程,像是在工厂里制造一个有形产品,主要探寻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是如何凝结到产品中,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又是如何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但是对于像看电视、玩社交媒体、刷短视频等这类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关注得就比较少,甚至因为这些是非生产性的所谓“休闲活动”,他根本就没有将它们看成是劳动。
因此,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些经济交换活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给出有效的解释,当然也就无法对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和伦理问题进行分析与批判。
大众媒体生产的产品是受众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加拿大的传播学者达拉斯·斯麦兹。他非常敏锐,对于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提出了一个貌似幼稚无知的问题:什么构成了可以大规模生产并且由广告商承担的传播商品的形式?换句话说,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生产的产品究竟是什么?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加拿大的传播学者达拉斯·斯麦兹。他非常敏锐,对于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提出了一个貌似幼稚无知的问题:
什么构成了可以大规模生产并且由广告商承担的传播商品的形式?换句话说,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生产的产品究竟是什么?
他认为之前的唯心主义学者们将传播商品看成是“讯息”“资讯”“图像”“意义”“娱乐”“导向”“教育”以及“操纵”。但是这些概念都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实体,而且只涉及表象。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媒介生产的商品是受众。
为什么这么说?这对于当下的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大众媒体通过内容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以及培养一种情绪,然后再将数目可以预测的受众卖给广告商,实现盈利。当然,这里所说的作为商品的受众,并不是指实体的人,而是指人的观看行为及其注意力。因为只有在大众媒介的条件下,民众才会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地阅读和观看固定的内容。所以说受众是被现在的媒体制造出来的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这对于当下的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
大众媒体通过内容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以及培养一种情绪,然后再将数目可以预测的受众卖给广告商,实现盈利。当然,这里所说的作为商品的受众,并不是指实体的人,而是指人的观看行为及其注意力。因为只有在大众媒介的条件下,民众才会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地阅读和观看固定的内容。所以说受众是被现在的媒体制造出来的产品。
斯麦兹认为劳动者在休闲时间里,不仅是按照传统理论所说的,通过恢复体力,以便更好地投入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与此同时,休闲时间的大众媒体消费,其实也是一种工作。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除了睡眠时间外,人一直在工作。而且要注意的是,受众商品被卖给广告商,广告商的目的是通过广告影响劳动者的消费决策。因此,大众媒体通过节目内容与广告的混合,实际上实现了对人们收入与闲暇时间的双重支配。
免费午餐式的观看,真的免费吗?
斯麦兹敏锐地提出了受众商品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揭示了媒体的商品化的秘密。他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不过也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比如受众的注意力和情绪过于分散,其实是很难被感知到的,真正交易的是报纸发行量、电视节目收视率等数据,所以抽象的注意力还要经过一个统计和数据化的过程才能成为商品。否则只凭媒体一面之辞,吹嘘内容如何好、受众如何多、质量如何高是没有公信力的。这就像市场交换需要货币这样一个流通中介一样。
比如受众的注意力和情绪过于分散,其实是很难被感知到的,真正交易的是报纸发行量、电视节目收视率等数据,所以抽象的注意力还要经过一个统计和数据化的过程才能成为商品。
否则只凭媒体一面之辞,吹嘘内容如何好、受众如何多、质量如何高是没有公信力的。这就像市场交换需要货币这样一个流通中介一样。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本来收视率这类数据只是对现实的一个反映,但是它慢慢就具有了独立性。这就像货币拜物教一样,虽然货币只是个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因为它能交换到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占有货币反而变成了许多人追求的目标。甚至有学者认为,发行量、收视率这些数据才是媒体生产的直接商品。到现在,数据、流量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前面讨论短视频时提到,甚至现在连流量都可以公开购买,这就是更加赤裸裸的商品化了。
斯麦兹虽然把媒体消费行为商品化的过程分析清楚了,但是却没有像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一样,继续讨论这其中的剥削问题和公平问题。这其中就留下了有一个可能似是而非的问题:受众从这类免费午餐式的观看中获得了什么?
斯麦兹虽然把媒体消费行为商品化的过程分析清楚了,但是却没有像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一样,继续讨论这其中的剥削问题和公平问题。这其中就留下了有一个可能似是而非的问题:
受众从这类免费午餐式的观看中获得了什么?
答案当然是内容带来的愉悦、放松、陪伴、知识的获取、社交、身份认同等收获,就像之前我们讨论过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里所描述的那样。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内容是否是受众需要的,还是它们只是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力而生产出来的诱饵?或者说,如果不观看媒体提供的这些内容,而进行其他活动,是否会带来更好的满足?这种收看或收听行为本身是否是被制造出来的需求?
答案当然是内容带来的愉悦、放松、陪伴、知识的获取、社交、身份认同等收获,就像之前我们讨论过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里所描述的那样。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内容是否是受众需要的,还是它们只是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力而生产出来的诱饵?或者说,如果不观看媒体提供的这些内容,而进行其他活动,是否会带来更好的满足?这种收看或收听行为本身是否是被制造出来的需求?
按照我们前面介绍的比较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以及后面要介绍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这些大众媒体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它巩固现有权力秩序,也是在对现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内容并不感兴趣,所以在当时并不能对这其中的不平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只是揭示了受众商品化的过程。
按照我们前面介绍的比较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以及后面要介绍的文化研究的理论,
这些大众媒体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它巩固现有权力秩序,也是在对现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但是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内容并不感兴趣,所以在当时并不能对这其中的不平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只是揭示了受众商品化的过程。
即便如此,这种将大众消费看作是商品的观点,在现实中还是能找到很多迹象。比如虽然很多人都选择躺平了,但是每天回到家还会强迫症似的看剧、看综艺、刷手机,有的时候还是非常累的,这是因为,即便你瘫在沙发上,其实仍然在为媒体打工。
即便如此,这种将大众消费看作是商品的观点,在现实中还是能找到很多迹象。
比如虽然很多人都选择躺平了,但是每天回到家还会强迫症似的看剧、看综艺、刷手机,有的时候还是非常累的,这是因为,即便你瘫在沙发上,其实仍然在为媒体打工。
点赞评论,都是一种劳动?
回过头看我们从今天的网络时代回看,斯迈兹的这些问题也受制于特定的媒介技术。对于广播电视等媒体来说,观看行为比较被动,人们就很难把看电视的“沙发土豆”和劳动联系起来。而到了网络媒体时代,用户除了被动观看外,还积极介入到生产与消费中。比如这两天日本排放核废水,就有业余人士拍视频去测中国海域的核辐射。所以现在只谈受众商品论就不够了,有学者开始用“劳动”的概念,比如“数字劳动”“网络劳动”等来描述这个过程。
回过头看我们从今天的网络时代回看,斯迈兹的这些问题也受制于特定的媒介技术。对于广播电视等媒体来说,观看行为比较被动,人们就很难把看电视的“沙发土豆”和劳动联系起来。
而到了网络媒体时代,用户除了被动观看外,还积极介入到生产与消费中。
比如这两天日本排放核废水,就有业余人士拍视频去测中国海域的核辐射。所以现在只谈受众商品论就不够了,有学者开始用“劳动”的概念,比如“数字劳动”“网络劳动”等来描述这个过程。
在网络平台上,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产消合一”,英文叫prosumption,就是把生产production和消费consumption两个词合在一起。这个概念最早由上世纪80年代赫赫有名的预言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中提出来,到现在真的成为现实。
在网络平台上,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产消合一”
,英文叫prosumption,就是把生产production和消费consumption两个词合在一起。这个概念最早由上世纪80年代赫赫有名的预言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中提出来,到现在真的成为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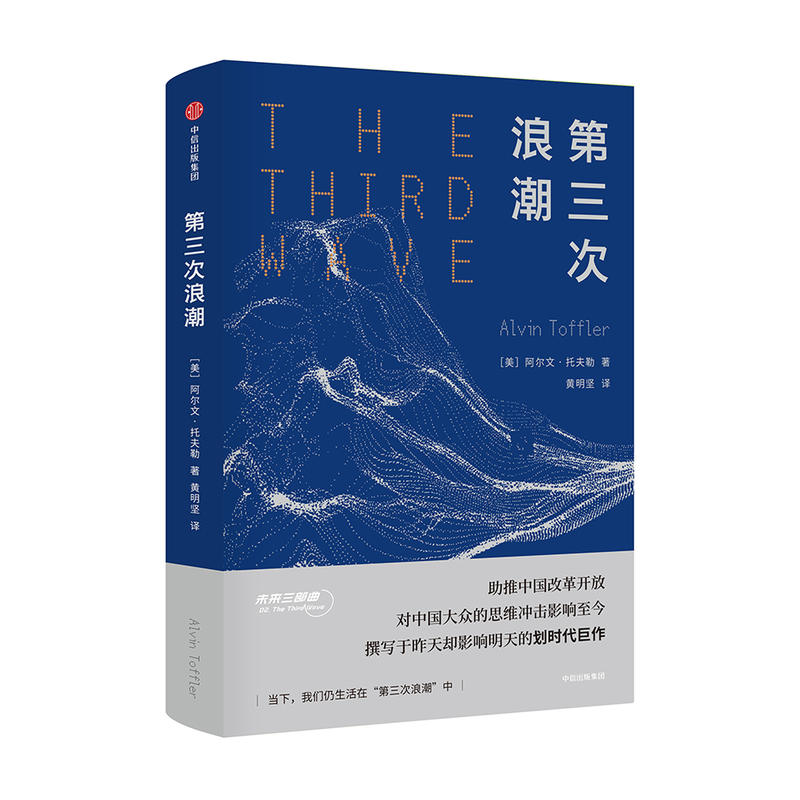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图源:bookschina.com
具体的意思就是,在网络平台上的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过去这两个界限清晰的概念变得融为一体。在大众传播时代,生产者都是专业人士,要经过专门的学习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现在的短视频拍摄者,很多并没有经过专业学习,也不讲究什么字正腔圆、形体语言、拍摄角度,轴线、穿帮和画面跳帧,过去的专业设备、技巧带来的壁垒都被打破了。专业的播音主持、电视编导、摄像专业出来的专业人士包袱太多,反而很难做出爆款的视频。
具体的意思就是,在网络平台上的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
,过去这两个界限清晰的概念变得融为一体。在大众传播时代,生产者都是专业人士,要经过专门的学习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现在的短视频拍摄者,很多并没有经过专业学习,也不讲究什么字正腔圆、形体语言、拍摄角度,轴线、穿帮和画面跳帧,过去的专业设备、技巧带来的壁垒都被打破了。专业的播音主持、电视编导、摄像专业出来的专业人士包袱太多,反而很难做出爆款的视频。
不过这些非专业的网红红得快,过气得也快,很难像传统的明星那样持续获得关注。但是对于平台来说,只要不停地有网红出现,它们就能够始终维持较高的流量。这反而比传统大众媒体风险更小。平台并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雇佣固定的工作人员,同时也可以不断地满足用户对于新鲜感的要求。
而平台用户来自不同背景,他们生产的内容也千奇百怪,大大超出了传统媒体所能够提供的内容,这些多样化的内容具有长尾效应,让用户有更多的选择。关键是,平台既不需要去生产这些内容,也不需要给绝大多数的内容支付报酬。这种外包式的劳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平台及资本的利益。
而平台用户来自不同背景,他们生产的内容也千奇百怪,大大超出了传统媒体所能够提供的内容,这些多样化的内容具有长尾效应,让用户有更多的选择。
关键是,平台既不需要去生产这些内容,也不需要给绝大多数的内容支付报酬。这种外包式的劳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平台及资本的利益。
即使是不直接生产内容的普通用户,其实也在为平台默默地劳动。比如点赞、评论、转发,发点自拍照,这些看似日常的操作,也在为平台一点一滴地带来人气和流量。
即使是不直接生产内容的普通用户,其实也在为平台默默地劳动。
比如点赞、评论、转发,发点自拍照,这些看似日常的操作,也在为平台一点一滴地带来人气和流量。
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只想睡前刷十分钟短视频或社交媒体,帮助自己入睡,但是很可能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按照斯麦兹的说法,这一个小时的关注也被转化成了流量和商品,被平台无偿地占有了。
“用爱发电”的游戏玩工
这个概念还可以往外延伸,数字化不仅消除了生产与消费的界线,休闲和工作的界线也在被消除,就连玩电子游戏,也可以成为劳动。爱尔兰学者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概念,他把游戏play和劳动labour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玩工”(playbour)的概念。
这个概念还可以往外延伸,数字化不仅消除了生产与消费的界线,休闲和工作的界线也在被消除,就连玩电子游戏,也可以成为劳动。
爱尔兰学者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概念,他把游戏play和劳动labour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玩工”(playbour)的概念。
他发现,游戏爱好者的参与不仅通过玩游戏,提高了游戏的人气,帮助品牌推广,同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到游戏的开发、修改与创作过程。现在一些大型的游戏不仅为玩家提供游戏场景,同时还通过推出编辑器,让玩家参与到游戏模组的开发过程。
比如非常曾经风行一时的游戏《反恐精英》就是模组化的典型案例。威尔乌公司在经典游戏《雷神之锤II》的3D浏览器内核的基础上,尝试基于模组的理念,1998年开发了游戏《半条命》的游戏。后来,在《半条命》的基础上开发出的《反恐精英》成为了其中最成功的模组游戏。

《反恐精英》游戏截图,图源:zhihu.com
普通用户可以利用游戏的引擎和工具,开发出新的地图和游戏场景。这种DIY式的游戏大大丰富了原有游戏的内容,延续了一个游戏的产品生命。我记得当年这个游戏风靡了很长时间,就是因为不停地有用户新开发的地图上市,这样就会让游戏常玩常新。
同时这些模组开发者不仅是游戏忠实的玩家和推广者,还会帮助游戏生产者发现漏洞,进一步完善游戏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很多人后来就成为了游戏公司的劳动力后备军。一直到今天,像《我的世界》这样的游戏也还在吸引众多玩家开发自己的玩法,这些改进又会为游戏添砖加瓦,增加更多的流量。
更关键的是,这些所谓的“生产性闲暇”都是“用爱发电”,这些无偿劳动为游戏公司节省了大量投入到研发与营销环节的人力物力,同时游戏公司还不用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方面的风险,游戏的核心内容和收益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公司的手中。
库克里奇进一步提出,这种休闲活动“劳动化”的推广,标志着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即弹性积累模式的出现。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玩家所投入的大量无偿劳动的基础之上,这些游戏和模组开发的时间,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时间一样,被游戏平台占有剥削了。
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可以补充马克思主义对休闲劳动的忽视,同时也将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贯彻到了文化生产之中,让我们看到传播过程不仅会生产内容,操纵心理和意识形态,它本身也是一个经济现象,涉及对劳动的操纵。
数据,还将带来什么?
数字时代用户的媒体使用行为除了为平台无偿提供内容外,还生产了一种新的商品,那就是数据。
大家可能都接到过各种推销或骚扰电话,甚至有些诈骗人员十分清楚你的背景,比如知道你的名字、年纪、家庭地址、职业等等。我们日常在工作和生活中登记的各种个人信息,被作为商品卖给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这个时代,个人数据也在成为一种具有价值的商品。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数据本身甚至成为平台所掌握的最重要的商品。
大家可能都接到过各种推销或骚扰电话,甚至有些诈骗人员十分清楚你的背景,比如知道你的名字、年纪、家庭地址、职业等等。
我们日常在工作和生活中登记的各种个人信息,被作为商品卖给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这个时代,个人数据也在成为一种具有价值的商品。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数据本身甚至成为平台所掌握的最重要的商品。
每一个人的浏览、购买、支付、位置、点赞、评论、发布等数字媒体使用痕迹产生的数据可能并不太重要,但是当千千万万网络使用者的数据加在一起构成大数据,就成为重要的资源。它的功能小到可以预测商品的走势,大到可以左右国家的政策与选举。
每一个人的浏览、购买、支付、位置、点赞、评论、发布等数字媒体使用痕迹产生的数据可能并不太重要,但是当千千万万网络使用者的数据加在一起构成大数据,就成为重要的资源。
它的功能小到可以预测商品的走势,大到可以左右国家的政策与选举。
目前中国各地都由政府牵头成立了数据交易所。这些数据被作为商品卖给各类营销机构,反过来对公民个体进行操纵。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普通人是完全不知情的,他们既不知道自己的数据被监控和收集,也不知道它们被卖向何处,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这个过程非常像马克思所描述的“异化”现象,就是工人自己生产的商品,反过来成为异己的力量统治生产者本人。
而且当数据与数据进行叠加,并且加以深度分析之后,就会产生新的数据,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能够影响决策,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
大家可能还记得2021年滴滴公司在美国上市被叫停的事件,这个后面的关键就是数据安全的问题,这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比如中国政府高层提出:要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数据,很多掌握在互联网企业手里,企业要保证这些数据安全。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6月10日通过,并于当年9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虽然从国家层面数据受到重视,但是从普通个人层面,我们仍然对自己的数据缺乏控制。有学者提出,要从作为资本的数据,向作为劳动的数据理论转型,强调普通用户对于自己数据的权利,不能让自己的隐私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陌生人或陌生机构使用。
最简单的,“被遗忘权”就是其中的一个。比如有一些对个人不利的信息在网上不断传播,还有像是个人不愿意发布的信息、照片等被恶意传播,但是目前似乎我们并没有什么办法要求这些信息从整个网络消失,这其实会造成很多人的一生都会背负着这些不良信息带来的污名。在隔壁翟志勇老师的《法律通识》节目中就有对这个权利更为详细的法律介绍,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听听。
那在个人对自己数据权利的掌握十分有限的现实中,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其实不太多,比如关闭社交媒体和短视频中的算法推荐,对用个人手机号、微信淘宝账号等换取一点小利益的应用和网站提高警惕,不要随便授权手机或应用使用个人隐私信息等。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建议,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那在个人对自己数据权利的掌握十分有限的现实中,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其实不太多,比如关闭社交媒体和短视频中的算法推荐,对用个人手机号、微信淘宝账号等换取一点小利益的应用和网站提高警惕,不要随便授权手机或应用使用个人隐私信息等。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建议,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我们今天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了媒介使用中的商品化与劳动现象,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平台对于劳动与数据拥有无偿占有与使用的权力,传播政治经济学通过其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权利不平等现象。
下次节目我们会反过来,讨论数字媒介对劳动造成的影响。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