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开放了解读权力后,人类的交流就能达成了吗?从撒播看对话的局限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上一期我们讲到,当把传播看成是一种传递行为时,以传播者为中心会导致传受双方无法真正相互理解的困境。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不再把别人的理解一定要符合“我”的看法作为传通的标准;如果我们看到多样的理解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和其中包含的平等与自由,是否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可以走出困境呢?或者,允许沟通中存在多元的价值,我们的生活是否会变得更加和谐?
这一集我们就通过“传播是一种撒播”的观念来讨论下这个问题。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传递与撒播之间的分歧,关键在于意义由谁来解读,或者说意义的解读标准由谁制定。
这里我想先讲个故事。你知道在中国互联网文化史上,最早的一个UGC(用户原创)的恶搞视频是什么吗?这要先从陈凯歌导演2005年的电影《无极》说起。
2005年底,一位在上海从事录音作曲及音像器材销售工作的网民胡戈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觉得不满意,于是他就使用这个影片的镜头,自己配音,把它恶搞成了中央电视台《法治进行时》那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命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其实这个视频的内容与原片没有必然关系,但是讽刺了原电影中的一些雷人的情节和设置。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2006年初,《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络迅速窜红,大家都下载下来观看,其它的知名度和网络搜索排名当时甚至超过原片《无极》。后来影响太大了,原电影导演陈凯歌也知道了,还公开发言说胡戈丑化了他的电影,要以侵权罪起诉他。
这件事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法学专家、文学批评家们都参与了进来,后者认为,这种视频的再创作应该算是一种对原作的创造性解读,或许它没有尊重原作的内容,但是也具有合理性。
这个故事中不同立场的争论,其实就很好的体现了我们刚才讲的传递观与撒播观之间的分歧。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家们说的这种超出原作者意图的解读,它是否真的合理,如果用传播学的方法来问的话,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是谁有权力决定传播内容的意义呢?
我们前一次节目介绍的传递观认为,传播的决定权在作者那里,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撒播观却认为,受众与传播者具有同等的权力。也就是说,胡戈这件事,在认为传播是一种撒播的学者那里看来,他的解读哪怕再离谱,也是正当的。
撒播的寓言:谁更有权力判定意义?
我们可以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传播是撒播”。在《新约·马太福音》里,耶稣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因为这里的土壤不深,发苗是最快的。但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还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里的种子就长得结实。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向他的弟子们解释说,这个撒种子的比喻是为了说明,就像不同的种子撒到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生长情况一样,耶稣的布道也是如此,不同的人听到耶稣传道的反应会不一样。
讲完故事,耶稣接下来还提出了自己的撒播信条,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就是说,不要因为听者的反应与我们预期的不一样,就把他们排除在传播之外。这个寓言的道理,说的大致就是撒播的含义。就是说传播要像撒种那样,不要过于执着于效果,顺其自然。
对于宗教宣传来说,这是一个在实际操作中非常有效的做法,广种薄收,向一切潜在的信徒传播天国的声音,而不必在意他们过去的立场和未来的结果,求同存异,有利于扩大其影响。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其中可能会存在的自由度,会不会造成误读?难道传播内容的意义就没有标准了吗?
这些疑问符合我们的常识,很多人可能和陈凯歌一样,会接受作者具有绝对的解释权,会觉得撒播观念背后的意义相对主义让他们很不舒服。但其实在现实中,内容生产者丧失解释权的情况经常出现。
我们前面讲过精神分析的例子,一个人自己做的梦,未必自己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一些行为,可能也要求助于专业的精神分析师。在这种极端情境下,专业人员的解释可能比原作者的解释更权威,甚至我们还要付费去了解这种解释。
现实中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就拿中国人最喜欢解释的一个文本《红楼梦》来说,各种说法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学科“红学”来研究。设想如果曹雪芹还在世,他会如何评价这些对他作品的解读?曹雪芹是否就具有绝对的裁决权?

“红学”家周汝昌
其实还真未必。事实上很多时候,内容的生产者自己也未必完全知道,自己的生产行为以及生产的内容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因为距离过近,当局者迷,作者也未必能够看清楚这个作品与时代的关系。同时,作者对一些无意的偏好、和时代加在他/她个人身上的影响,也未必有明确的意识。
德里达的“双重阅读”:没有标准答案
关于这个问题,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学者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他干脆提出了一个“双重阅读”的概念,他的结论是,其实作者根本不拥有全部的解释权。
他的这个双重阅读,大意是说,一方面读者要去揣测传播者的意图,也就是文本传达的思想与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读者也可以作出超越作者的解释。因为那些“在现场”的、被我们看到的文本符号,并不能自动地解释所有的意义,它还要依赖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不在场的符号与意义的网络才能够说明和定义自己。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比如经典的诗歌鉴赏案例,贾岛犹豫使用“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王安石把“春风又到江南岸”改成“春风又绿江南岸”。无论他最后选择了哪个字,其实都是那个没有被选中的字,才衬托出最后被选中的字的独特之处,以及作者个人的风格倾向。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从字里行间读言下之意的意思,也就是说既要关注人们说了什么,也要关注他们没有说什么。
不过,这些不在场的符号与意义网络永远没有办法穷尽,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在不同的语境下,我们会有不同的网络作为意义解读的参照,所以这个对于在场的意义的解读,也就永远是流动的,没有标准答案。
德里达还进一步提醒我们,即便是第一层的阅读,就是对作者本意的阅读,我们对这个意义的把握也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因为作者的意图也总是通过符号的中介在呈现给我们,有中介就会有噪音,说到底也是对文本的阅读,这又回到第二层阅读的矛盾里去了。它同样会使得阅读和解释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哪怕字面意思的理解,也会存在误读。打个极端的比喻就是,你怎么知道我说的鸭子,不是你说的鸡呢?
所以按德里达的这个双重阅读的说法,意义就是不存在标准答案的,因为解读的差异不管是在第一层,还是在第二层,总是存在。
巴尔特的“作者已死”:把解读的权力交给读者
法国文学批评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的概念比德里达更形象一点。他把文本分成两种:一种是只读的文本,另一种是可写的文本。
只读的文本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僵化的文本,接受者只能被动地揣测作者的意思,这种文本有标准答案,它的意义非常封闭。而后者则是可以让读者最大限度参与的文本盛宴。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作者不再有权力去控制意义的自由发展,解读的权力应该交给读者,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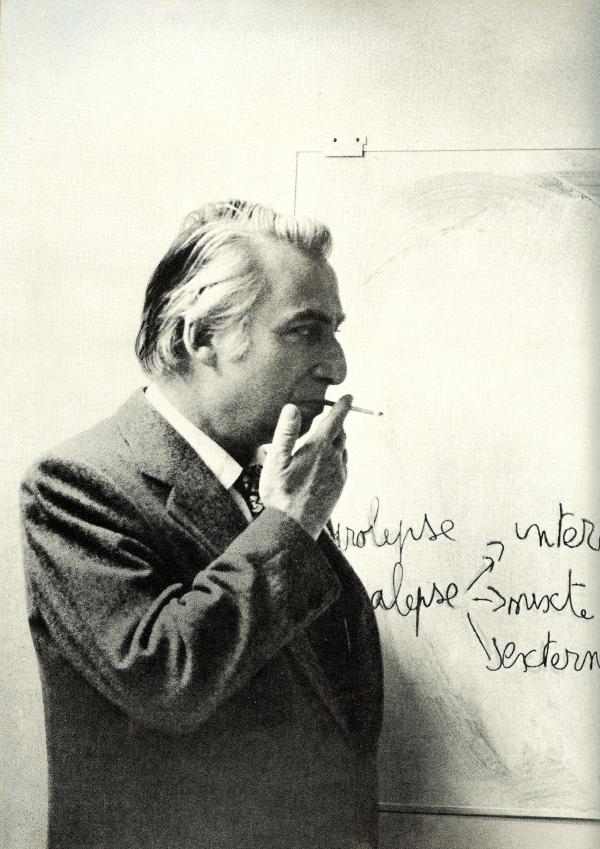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
巴尔特甚至极端地提出,作品先于作家,作家本身只是他的文本的代言人,巴尔特为什么这么推崇可写的文本?因为他认为在只读的文本中,我们只能获得一种温馨如归的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式的感受,这是一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轻度的快乐(plaisir);而在可写的文本中,我们获得的是一种无法言状的极乐(jouissance)的感觉。巴尔特在这里说的,其实是标准答案不值得追求,或者说对它的强求会带来危害。
顺便说一句,前面谈到的中国传播观念里的水的隐喻,在中国的传播传统因为非常注重同一性。这让我们的语文教育就特别重视对作者意图的解读,追求统一的标准答案和文章的中心思想。作为基础训练,这个做法固然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这种阅读方式看成唯一正确的阅读方式,只追求背诵和揣摩可疑的作者的原意,可能就剥夺了孩子们本该具有的创造性与多样性。
顺便说一句,前面谈到的中国传播观念里的水的隐喻,在中国的传播传统因为非常注重同一性。这让我们的语文教育就特别重视对作者意图的解读,追求统一的标准答案和文章的中心思想。
作为基础训练,这个做法固然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这种阅读方式看成唯一正确的阅读方式,只追求背诵和揣摩可疑的作者的原意,可能就剥夺了孩子们本该具有的创造性与多样性。
而且,在这样一种追求标准答案的阅读习惯的长期塑造下,我们也就不大会容忍不同的解读,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现在互联网的舆情讨论经常走向极端的原因。其实很多思想的创新,就是源自于有意无意的误读,这就像是基因传递中,如果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那也就不会产生新的特性与新的物种。
对话:一个不必当真的传播隐喻
但好在,人们对于传播的理解或者说需求,一直在改变,它几乎与媒体的发展是同步进行以及互相作用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撒播这种一对多,只求扩散,不问结果的传播方式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熟悉的大众传播?
什么是大众传播?比如电视,千家万户看的是同一个节目,除了换台以外,观众也不能控制播放的内容。报纸也差不多,所有人看的是同一个内容,读者有疑问或者发现问题,也无法及时反馈。
因此,过去人们一直批评大众传播在很多方面不如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认为它没有办法反映接受者的意见。所以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卢梭,都认为面对面的口语传播优于文字传播,也就是撒播或者大众传播,因为撒播或大众传播缺乏反馈,造成不同的接受者会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但是美国学者彼得斯不太同意柏拉图和卢梭的看法,他认为,面对面的对话虽然表面上会让我们达成相互理解,但是也并非十全十美的传播形态。接下来我们不妨通过思考“对话”的缺陷,来看为什么撒播或大众传播这种所谓缺乏反馈的传播,其实是更加平等和自由的一种方式。
首先,对话的要求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要求获得平等的地位和全身心的关注。比如你要和我对话,而我由于各种原因拒绝了这次对话,你就会觉得我不给你面子,甚至在道德上可以谴责我对你缺乏尊重。所以对话要求的背后有一种道德上的霸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所有人的对话请求呢?这不是一种强制吗?
美国作家、《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位律师事务所的抄写员巴特比的故事。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
巴特比是律所新招的一位抄写员,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按照律师的要求,把律师与客户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写完之后,律师想检查一下他的工作,让他把记录给他读一下。巴特比说,“我倾向于不给你读(I prefer not to read)”。
律师有点生气,说你是不愿意给我看吗(You will not)?巴特比回答说,我不是不愿意,也不是拒绝你,当然也不是愿意给你看,只是选择不给你看。这背后的意思是,我没有任何明确的主观态度,只是不想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这就把律师给整懵了。
律师有点生气,说你是不愿意给我看吗(You will not)?巴特比回答说,我不是不愿意,也不是拒绝你,当然也不是愿意给你看,只是选择不给你看。这背后的意思是,我没有任何明确的主观态度,只是不想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
这就把律师给整懵了。
大家可能听过鸦片战争中,英国人要求要么开战,要么投降,清政府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有个非常有名的回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其实这些态度的后面就是我不想做任何主动的选择,你们给的选项我不愿意接受,甚至我根本就拒绝做选择,因为我一做选择就会掉进你们设置的两难陷阱里面,我更愿意躺平不作任何反应。

叶名琛
相信不少人会有这种在to be or not to be间做选择的困难。巴特比的这种态度,其实就是针对对话的霸权提出的一种反抗策略,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有没有其他第三种选择?巴特比这个表面上看上去非常奇怪的回答,反映了人们意识到了对话霸权背后的套路,试图摆脱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两难困境。大家下次遇到这种困境时不妨学习下巴特比,别轻易接受别人问题中的二选一的前提假设。
相信不少人会有这种在to be or not to be间做选择的困难。巴特比的这种态度,其实就是针对对话的霸权提出的一种反抗策略,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有没有其他第三种选择?
巴特比这个表面上看上去非常奇怪的回答,反映了人们意识到了对话霸权背后的套路,试图摆脱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两难困境。大家下次遇到这种困境时不妨学习下巴特比,别轻易接受别人问题中的二选一的前提假设。
其次,对话还有一种排他性。如果我与你对话,同时就意味着放弃与其他人的对话,对于其他交流对象存在歧视性的对待。比如我不能一边和你交谈,一边和旁边的人说笑,或者还在手机上回复其他人。这会让人感觉不舒服,认为我不尊重你。
人们要求的是对方聚精会神地倾听与回应,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你,而拒绝世界上其他所有人。所以彼得斯说,这种对话和爱欲非常像,都是排他性的。
再次,按照上面的标准,真正的对话只存在于一对一的个人之间,无法胜任今天规模巨大的民主社会的集体交流。一对一的交流适宜小城镇的日常生活,但并不适应今天这样复杂多样的社群,更不要说国家层面的交流。
我们经常听到说政府或者组织与公众之进行“对话”,但是机构与个人之间是无法真正做到平等的、爱欲似的沟通的,机构或者组织对公众只能撒播,无法对话。所谓对话,只不过是个隐喻,不必当真。
最后,如果我们把面对面对话作为交流的目标或者交流的理想,这就导致我们会对交流的过程与结果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总是希望有能够达到灵魂层面的对话,一旦达不到这个目标,就会导致对交流结果不满,或者丧失对交流的信心。
所以彼得斯认为,我们首先要抛弃那种不切实际的、只有一个标准的传播目标。传播不是心连心,而是手拉手。不一定所有的传播要追求传播的结果,平等、宽容、高效地进行撒播(dissemination),让接受者拥有自由解读的权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撒播的伦理与政治
到这里我们发现,尽管和人际之间的对话相比,以大众传播为代表的撒播具有平等、宽容和高效的特征,但是彼得斯也对撒播的缺陷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撒播观念对交流结果的漠视,还是会使社会难以达到共识与团结,而共识和团结对一个社会又非常重要。
那这听起来会不会很矛盾呢?究竟在相互理解和自由解读两种观念之间如何选择?究竟是选择自由还是团结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但是这种困境其实不断地提醒我们,交流的背后是一个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它涉及到接近权和可获得性,而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内容有没有效果的接受心理问题或者语义学的问题。
那这听起来会不会很矛盾呢?究竟在相互理解和自由解读两种观念之间如何选择?究竟是选择自由还是团结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
但是这种困境其实不断地提醒我们,交流的背后是一个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它涉及到接近权和可获得性,而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内容有没有效果的接受心理问题或者语义学的问题。
下一次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再谈一谈传播效果与通过信息进行控制的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推荐阅读
1.约翰·杜伦·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2.罗兰·巴尔特:《文之悦》
3.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
4.Derrida, Disse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