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技术垄断:媒介在替人做决策吗?| 柏拉图、海德格尔、温纳、波兹曼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
前面我们用两期节目介绍了媒介的历史,这一期我们要谈一谈媒介和社会的关系,说下几位重要的哲学家和传播学者对媒介技术的看法,比如柏拉图、海德格尔、写出了《自主性技术》的美国哲学家温纳,还有大家熟悉的波兹曼,他们如何看待媒介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媒介与社会的两种看法
说起媒介和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些观点分成两个大的类型,这两个类型是比较极端的,一个叫做媒介决定论,一个叫做社会决定论,当然这两类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立场。
社会决定论认为是社会最终决定着媒介技术的发展。首先它认为是社会因素导致我们人类产生了某种需求,或者是产生了某个文化,这个时候会促进我们去发明某个媒介,或者抑制某个媒介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人类想要进行远距离交流,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发明电报、电话,甚至于我们今天的互联网。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才会促进这些媒介技术的发明。
所以不同的文化因为它的需求不一样,也会出现差异。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互联网最早诞生在美国,而不是诞生在中国,或者是诞生在苏联。曾经有过这样的研究,苏联在互联网的发展早期,其实它的技术比美国好,而且很早就有人想要去发明互联网,但是因为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不允许建立这样的一种网络,所以最后就落后了。
而美国因为有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所以有一批激进分子,他们就想去制造一个平等的、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种乌托邦,所以它促进了最早西海岸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当然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求,促进了互联网的产生,这个都叫做社会决定论。我们放在后面再详细介绍。

1966年,反文化运动人士聚集在格林威治村
什么是技术决定论?
我们今天先讲技术决定论。所谓的媒介决定论认为媒介技术决定社会的发展。一般来说就是当某个媒介发明出来之后,这个媒介会影响社会的某个方面。
比如说媒介可能会影响知识在社会中的分配,或者媒介会影响人的感觉器官的平衡。还有的认为媒介会影响我们人类行动的情境,或者是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进而就会影响社会的进程,使社会朝着媒介所偏向的方向发展。这个就叫做媒介决定论。
媒介技术决定论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理论。在历史学里面曾经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马镫它的发明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转型。大家去看早期的骑兵,其实它是没有马镫的,比如说古希腊、古罗马,他们的骑兵主要是用于运输,或者是在战争中间去冲击对方的阵型。

蒙古型鬼纹马镫
因为没有马镫,所以人不能够很平稳地坐在这个马上,两个手它得抱着这个马不能放开。但是有了马镫之后,手就被解放出来了,就可以射箭,可以挥舞着武器,这一下战斗力就提升。
所以马镫在蒙古人发明之后传入到了欧洲,它就促进了欧洲骑兵的战斗力的提升,同时就产生了所谓的骑士阶层,这个骑士阶层整个就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军事的格局,出现了封建社会、骑士社会。这是在历史学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理论,就是小小的一个马镫的技术改变了欧洲的这个历史进程。
其实在传播学里面也有非常类似的观点,就认为是媒介它改变了整个社会,那么媒介到底对社会的影响是大还是小?是善还是恶?这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不好一概而论。
但是恐怕我们生活中间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评价。比如说小朋友考试成绩下降了,肯定就会有人说,肯定是玩游戏导致的。还有比如说网上出现了网络暴力,有人会说这就是社交媒体造成的,所以媒介经常成为很多社会问题的背锅侠。
当然从我记事起,电视、电子游戏、网络、手机轮番成为被指责的媒介对象。但是比如说书籍、文字,它的形象一直就很正面,喜欢看书,总会被人夸奖。所以很少有人会抱怨书写文字造成了社会问题。
但是果真如此吗?其实当我们把这个历史翻回到2000多年前,你会发现书写文字也替社会问题背过锅。
文字也曾被柏拉图评价为没有智慧的媒介
比如说我们去看《柏拉图对话录》里面有一篇叫《斐德罗篇》,在这个里面就对文字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批评。在这篇对话录里面,提到有一个精灵叫做忒伍特,忒伍特是第一个发明了数目,发明了计算几何、天文,他还发明了跳棋、掷色子,尤其是他发明了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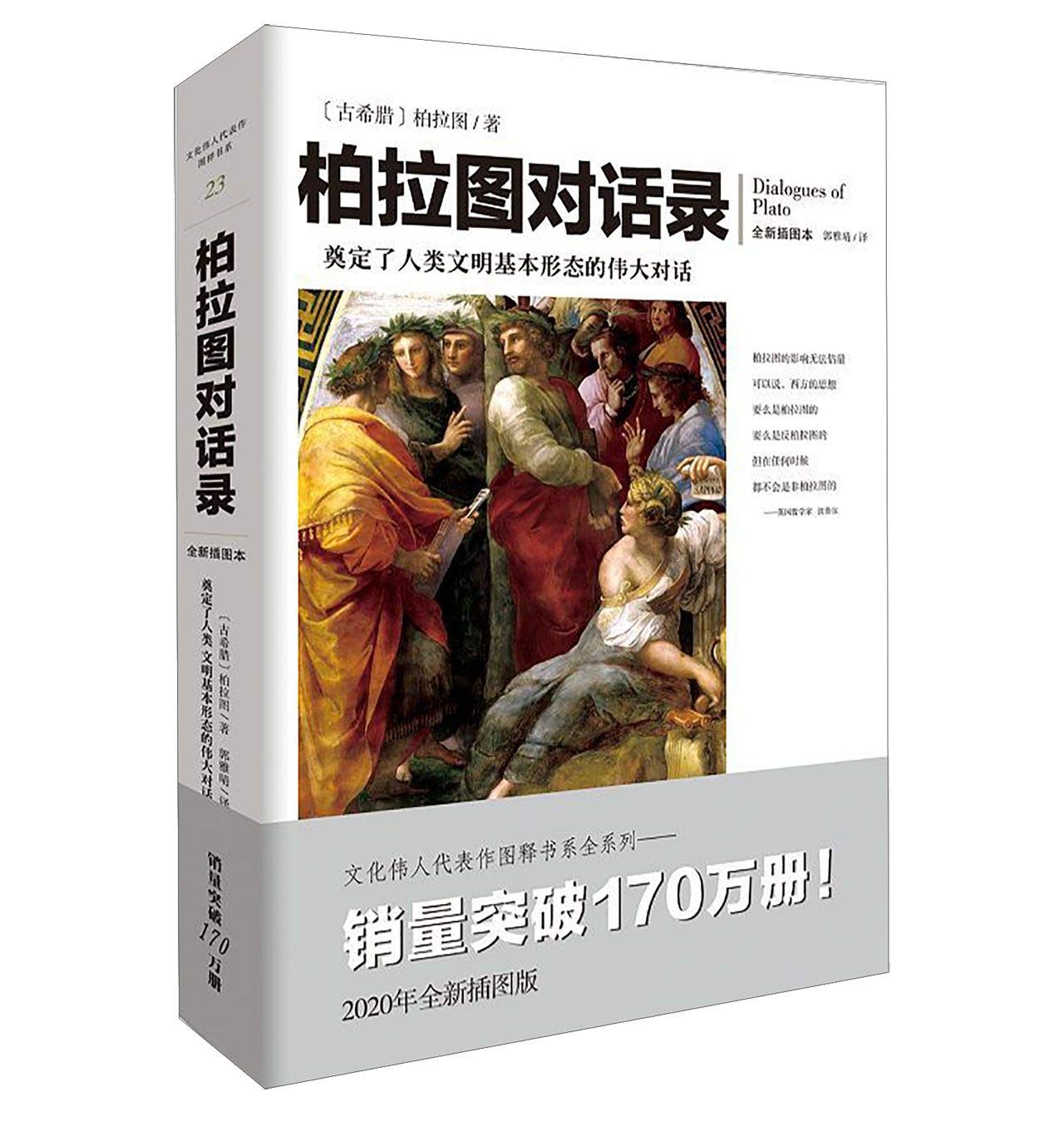
《柏拉图对话录》,重庆出版社
当时整个埃及的国王是叫做塔穆斯,这个忒伍特就去见塔穆斯,去展示他发明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讲完这些发明之后,这个时候忒伍特就给他介绍,说文字这个东西好,这个是学识,它会使整个埃及人更有智慧,回忆力更好,因此,这项发明是增强回忆和智慧的药。
这个时候古埃及的国王塔穆斯他非常的有智慧,他对文字做了三个判断,第一个,他说你有能力去发明这个技艺,这是一回事,但是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个技艺,到底这个技艺对人带来好处还是坏处,这个事情,发明技艺的人就不一定有绝对的发言权。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大家经常去听那些技术发明者,他们怎么来讲这个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技术的使用超越了发明者他本身的想象,包括电影的发明者、电话的发明者,其实最早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媒介技术的使用都和后来不一样。
比如说电影,当时爱迪生想的是大家可以在街上建一些小小的亭子,我们进去之后去看一段电影。电话最早是作为电报的替代品,很多人会认为电话可以用来听音乐、听新闻,等你想消遣的时候,把电话拿起来拨个号,你就能听到一段音乐或者听到一段故事。这个我们知道,这后来是广播的功能,所以最早的这些发明者,他们其实并不清楚他的发明能够为社会带来什么。

街边的镍币影院
这就是国王塔穆斯对忒伍特和文字的第一个判断。接着,塔穆斯还讲了第二句话。
他说,你作为文字之父,出于好意把文字能做的事给说反了,它不是为了回忆,而是为了记忆,回忆和记忆是两回事儿。记忆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的记忆,回忆它包含着对这个知识的运用。
所以他就讲了第三句话,他说你让学习者得到的是关于智慧的意见,而非智慧的真实,所以他们是显得有智慧的人,而非真正有智慧的人。
这是古希腊人的一个区分,就是意见和事实。因为对古希腊人还有古罗马人来讲,意见它是多变的,是主观的。而事实、真实,它是实体,是不变的东西。所以他讲说你发明了文字,实际上只是获得了很多关于智慧的意见,并没有增长智慧本身。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尖锐,我们今天当然相对于柏拉图、相对于古希腊时期的人来说,我们有很多知识,但是我们是不是比柏拉图、苏格拉底更有智慧?我们通过书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科学,但是这样的一些科学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通过思考获得的。
所以塔穆斯讲文字可能只是让我们显得有智慧,而并非真正有智慧。书写文字其实它没办法让我们交流,没办法让我们提问。当我们看到书写的文字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作者那里直接获得反馈,所以他没法确定真相,他就不像面对面的口头交流。
所以塔穆斯讲文字可能只是让我们显得有智慧,而并非真正有智慧。
书写文字其实它没办法让我们交流,没办法让我们提问。当我们看到书写的文字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作者那里直接获得反馈,所以他没法确定真相,他就不像面对面的口头交流。
大家想一想柏拉图的对话录中间,苏格拉底不停地跟人对话,在对话中间去一点一点的发现真相,一点一点的推出谬误。如果你面对的只是一篇文字,你就没法对他提问,没法一点一点的去往下找到真相。
所以对柏拉图来说,书写文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交流方式,它比不上面对面的口头传播,比不上面对面的口头质疑和提问。这是柏拉图对于文字的意见。
可以说,他是从技术的角度去评价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他是最早的技术决定论者。当然,柏拉图对文字的看法,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因为那会的文字、语言还是新事物,这个时代的人,更崇敬的还是口语。
海德格尔:到技术之外,看媒介带来了什么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去看今天的媒体,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限于我们今天的某些偏见。
这一点,大家熟悉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当然,海德格尔他不是直接讨论媒介技术,但是他关于技术的一般讨论,经常被大家引用,来讨论媒介技术的影响。
那么海德格尔他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技术的本质不等于技术本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把眼光放得更宽一些,到技术之外,到技术和我们人的关系中间去看媒介技术到底带来了什么。
他对技术提出了正反两方面。一个技术,他认为有去蔽的作用。所谓的去蔽就是去除遮蔽,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表象之外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通过望远镜,这是一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肉眼看不到的。包括我们使用网络,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播放的节目。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摄像头,每个人都可以监视这个社会,所以网络经常让我们去发现真相。
这是海德格尔讲的技术的好的一面。但是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评可能是大家谈的最多的。
他发现,现代的媒介技术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切近性,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人和人拉得很近。我们有飞机、还有各种高铁交通工具,让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见面。甚至我们今天通过网络,我们可以不用身体移动,直接就可以跟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马上接通。所以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由于技术的介入,看上去变得非常的近。
但是这种切近性,是不是真的把人和人的关系拉近了?海德格尔是持否定意见的。有可能我们今天联系的人越多,联系得越密切,有可能我们的关系越疏远。
特克尔有一本书叫做《群体性孤独》,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越连接反而越孤独。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媒介技术越发达,好像大家越愿意宅在家里,越不愿意和人去交往,它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这是海德格尔讲的技术的切近性,不一定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切近性。

《群体性孤独》,浙江人民出版社
集置:技术是让我们看到真相还是让我们失控?
另外,海德格尔他认为技术的影响是系统性的,甚至于说你不使用这个技术,并不等于就不受这个技术的影响。
他就讲技术它是一种集置,集就是集合的集,置就是位置的置。或者是有的把它翻译叫座架,座就是座位的座,架就是架子的架。就是它把我们整个社会放到某一种框架中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使用技术并不等于不受其影响。
海德格尔举过一个例子,他就说,我们要修一个水库,修一个水库它不光是影响河流的这一段,它可能会改变整个河流的生态,它可能会改变供电的情况,它可能会改变周围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
所以一旦使用这个技术,我们等于就把自己放到了这个技术所不能控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中。所以他还有一句话,当你使用技术,当你将技术作为一种集置或者座架的时候,人和物就变成了技术的存量,我们多多少少变成了技术的附属品,我们没有办法去操控、跳出这个技术的影响。
所以一旦使用这个技术,我们等于就把自己放到了这个技术所不能控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中。
所以他还有一句话,当你使用技术,当你将技术作为一种集置或者座架的时候,人和物就变成了技术的存量,我们多多少少变成了技术的附属品,我们没有办法去操控、跳出这个技术的影响。
所以这是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看法,大家看是不是比较悲观,海德格尔代表着一种对技术的悲观主义,但是他的悲观主义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技术的发展,确实在某些方面让我们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我们不能够操控自己。
我们使用手机,或者是即使你不使用手机,你思维的逻辑也在变得越来越接近手机的思维方式。我们被卷入到了一个越来越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间,停也停不下来。这就是海德格尔讲的技术本身对我们深刻的这种影响。
技术的倾向:大数据是集权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技术本身有善恶吗?有的人讲说技术是中性的,我们看它如何使用,就像刀不会杀人,只有使用刀的人才会杀人。所以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技术是一个纯粹中立的工具,它的善和恶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技术。
美国的哲学家温纳,他就提出来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任何的技术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它会让某些人得利,某些人失利。
比如说他就讲纽约长岛,有个公园大道上修了200多个过街天桥,但是过街天桥修得非常低,公共汽车过不去,只能小轿车过去。

长岛公园中的低桥
后来他就发现,这个设计者罗伯特·摩西,他在当初设计的时候,他就是故意把这个桥做得很低,不让公共汽车通过,这样只能拥有小汽车的上层和中产阶级才可以通过,当然他们就可以享受长岛公园大道附近的这些公园、海滩,一般贫穷的阶层你就进入不了。
所以你看这里面的桥,它是一个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是有倾向性的。类似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豪斯曼男爵当时在19世纪中期对巴黎城市的改造,当时在路易·拿破仑的指导之下,他就修建了非常宽阔的巴黎街道,看上去很气派,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是有它的倾向性的。
因为在此之前1848年,巴黎市民爆发了街垒战对抗政府。如果你把这个路修得很宽的话,市民就很难进行街垒战了。如果很窄,他就可以修建堡垒,在那对抗军队。所以这样一个路看上去是很中性的,但是实际上,它对统治者是有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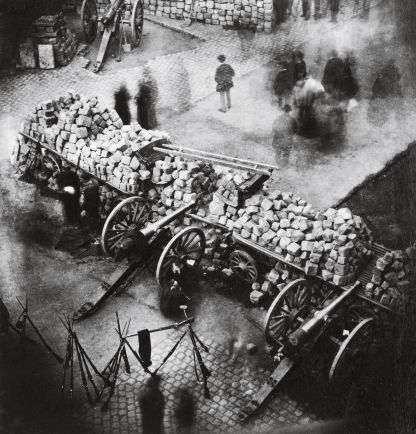
街垒战中的路障
所以温纳认为有些技术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有些技术它是民主的,有些技术它就是集权的。比如他说轮船、铁路,这样的技术就带有集权的性质,因为轮船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不能各行其是,不然就会出事故。
温纳还举了一个例子,原子弹,他说原子弹这个技术一定是要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的。所以大家看美国的总统,出来都会拎着一个原子弹的箱子,一旦有了紧急情况,他可以授权,马上发射原子弹。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对你发射了原子弹,你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确保相互摧毁,这样你这个原子弹才有威慑力。那就必须要求一个人来做决策,所以这个风险就非常之大。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大数据,其实也有集权的倾向,因为只有掌握所有的数据,才能称之为大数据。所以大数据本身,它就具有了某种非民主的特征。
所以我们在使用技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难控制。有些技术我们可以控制,比如说你们家的菜刀,这你可以控制,但是有些复杂的技术,就是任何人都难以控制的。我们今天的技术就开始倾向于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温纳也安慰大家,实际上技术的发展也不是某个人能够决定的。
所以他有一个观点,叫做技术的漂迁论。他说,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它有它自己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本身,它可能缺乏一个明确的力量,所以它是随机的。可能很多的偶然性加在一起,会形成技术最终的结果。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安慰大家,其实也不必担心技术背后有一个邪恶的人在控制它,因为我们经常会想到,某一个科学家或者某一个政治家去操纵技术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互联网,互联网就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这个技术其实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集体,是很难控制它的发展的,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在中间起作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任何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都很难决定。
波兹曼的技术垄断论
媒介影响的这种不可控性,波兹曼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不过他是从人类文化类型的角度上来讲的。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波兹曼写的《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其实他的“技术三部曲”,还有一本结尾的书叫做《技术垄断》,这本书可以说代表了它对于技术和媒介决定论的最典型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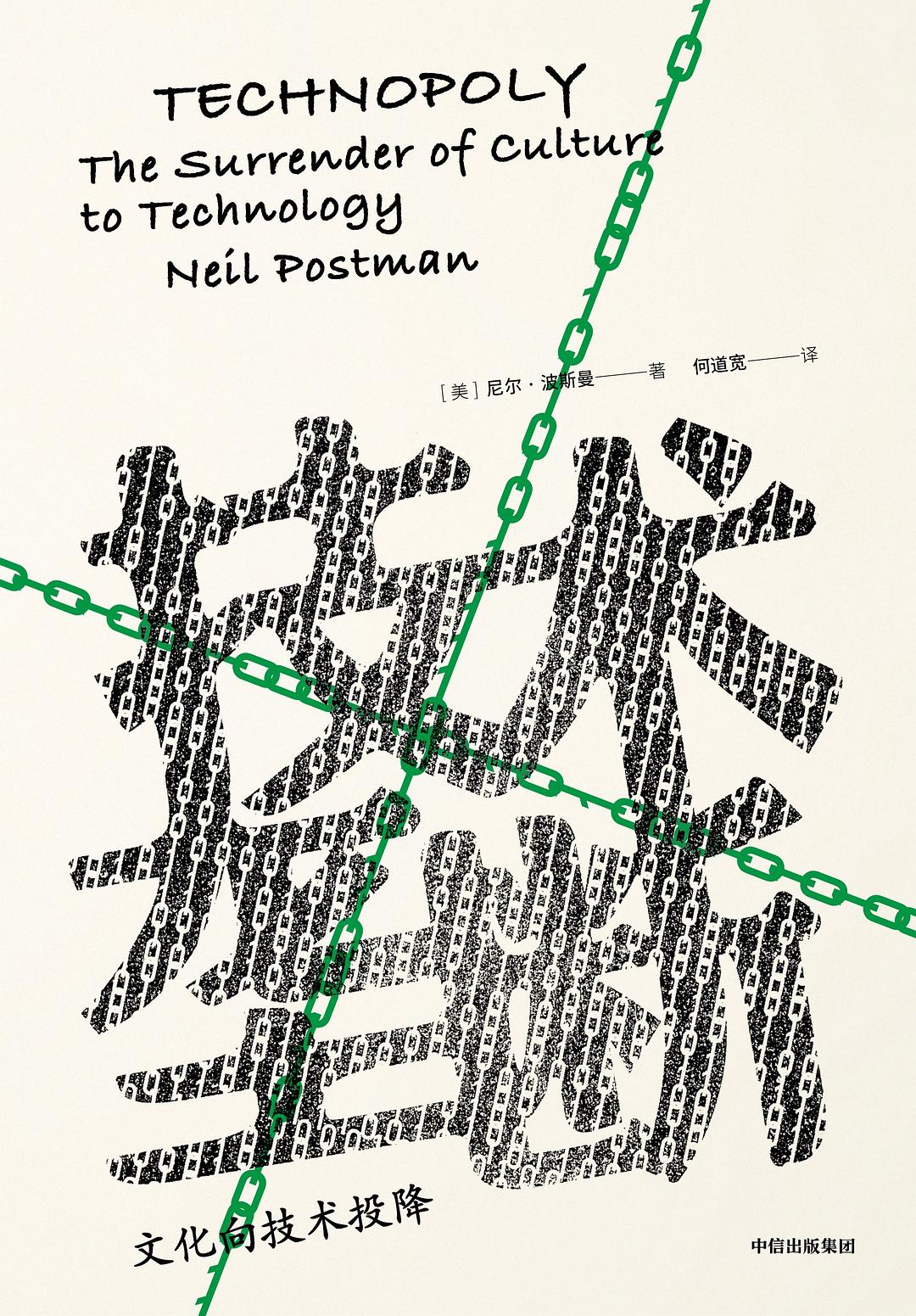
《技术垄断》,中信出版社
波兹曼在《技术垄断》里面就谈到,我们和技术的关系,我们按照技术的重要性,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文化,一个叫做工具使用的文化,一个叫做技术统治的文化,第三个叫做技术垄断的文化。
所谓工具使用的文化,就是我们在使用一个工具的时候,它是完全听从我们文化的需求来使用。这个主要是在中世纪以前,它不会对我们的社会构成比较大的挑战。当然波兹曼讲这也不绝对,比如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非洲,人类学家就发现了,有一个部落,当这个部落里面男女发生关系之后,他们就要重新去生这个火,重新生火你就要借火种,所以你就要到别的帐篷里面去跟人借火。
所谓工具使用的文化,就是我们在使用一个工具的时候,它是完全听从我们文化的需求来使用。
这个主要是在中世纪以前,它不会对我们的社会构成比较大的挑战。当然波兹曼讲这也不绝对,比如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非洲,人类学家就发现了,有一个部落,当这个部落里面男女发生关系之后,他们就要重新去生这个火,重新生火你就要借火种,所以你就要到别的帐篷里面去跟人借火。
所以一借火大家就知道,这对男女他们刚才在做什么,所以在他们的部落里面,通奸、婚外情很少发生。但是后来传教士就把火柴引进去了,有了火柴之后,他们可以自己点火柴来生火,这样就不用去跟别人借火了。
他说这一下就使得他们部落的文化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就胆子越来越大,所以礼崩乐坏。所以他讲就说,当我们的技术引进到这样的一种工具使用文化的时候,会对他们造成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第二个阶段他把它称之为叫做技术统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世界和象征世界就要给工具让路,它们要帮助工具发展。但是在这个时期,工具还没有被整合进文化之中,对文化还没有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阶段他把它称之为叫做技术统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世界和象征世界就要给工具让路,它们要帮助工具发展。
但是在这个时期,工具还没有被整合进文化之中,对文化还没有很大的威胁。
比如说,过去这个时钟都是靠教堂的钟声,或者是靠宫廷的钟声,其实这个在中国也是一样,我们有钟楼、鼓楼、晨钟暮鼓来告诉大家时间。
但是有了机械时钟之后,大家就在自己家里面听自己家里面的时钟的指挥,就不再听教堂的统一时间的指挥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产生了新的观念,就是个人主义的观念。所以他讲说在中世纪开始,技术开始越来越重要,开始对既有的文化构成了挑战,但是我们的文化和技术还是相对独立的。
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他讲的技术垄断的文化,而在这个时候传统的世界观就消失了。技术清除掉一切替代性的选择,也就是说技术彻底征服了文化。波兹曼认为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管理学家泰勒发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这本书在1911年问世。
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他讲的技术垄断的文化,而在这个时候传统的世界观就消失了。技术清除掉一切替代性的选择,也就是说技术彻底征服了文化。
波兹曼认为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管理学家泰勒发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这本书在1911年问世。
在这本书之后,我们把效率放到了一个优先的位置。当然,再往前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孔德,推崇一种科学至上的这种世界观,所以一切都变成了通过科学、通过技术来解决的问题。
技术开始替代了人的决断,替代了人的决策。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医疗,你会发现过去的医生都是望闻问切,他要问病人,你的感觉怎么样?所以他看的是病人,但是现在的医院、现在的医生,进去之后,首先让你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拿着检查的数据来对你做判断。
所以他研究的是这个疾病,而不是这个病人。病人自己的信息不可靠,机器才是可靠的。这个从听诊器的发明开始,就开始不依赖于病人自己的报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看病,要经历很多的医疗检查,因为有了这些机器的数据,他才能够说我做出的决策有所依据,而不能根据个人的经验来做判断,因为这个经验我们认为不可靠,或者是当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这就是一种技术文化的影响,大家都相信机器看到的东西,相信机器所得出的客观的结果。各种经济的发展我们都要看数据,要看统计,甚至于政治,我们也要看民意测验的数据。心理学也是一样,我们把一切都交给心理专家,他们来进行诊断。
不要因为媒介就忽视了其他因素
这是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关于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当然技术决定论也有些人认为它其实是一个稻草人,把某些观点给推到了极端化,变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荒谬。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取决于很多的因素,技术在某个方面或者在某个时段,它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总是如此。
所以也有人把这个技术决定论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硬技术决定论,就是认为技术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第二种叫做软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技术先决定我们的文化,决定人的某种行为方式或者是思维方式,是我们出现某种偏向,这样一种偏向在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还有一些人提出来,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多因一果的现象,也就是说技术其实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我们不能说技术直接决定了某个结果,它是和许多其他因素一起产生的结果。
这些也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对于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评价。在这里简短补充这些观点,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我们对媒介技术的研究,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是从媒介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会夸张、夸大媒介技术的影响,会把媒介技术单独拿出来讨论。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我们前面开篇提到的那个普遍现象,一旦出现社会问题,媒介总是很容易成为背锅侠的原因。这样看问题,就是单因素的决定论,也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媒介决定论。
所以各位听友在后面的节目中间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我们是一个讲媒介的节目,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其他的因素,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认为其他的因素就不起作用。另外,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尽可能多地讲不同学派的不同看法的原因,就是希望不要给大家误导。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推荐书目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
柏拉图,《柏拉图四书》,刘小枫译,三联出版社,2015.
马丁·海德格尔,《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孙周兴、张灯译,商务印书馆,2018.
兰登·温纳,《人造物有政治吗?》,《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